原创 我方或收到一笔巨款,特朗普吞进去的万亿关税,可能全都得还回来
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他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谓精准命中了美国铁锈地带选民的关切点。这些曾经繁荣的工业区因全球化浪潮而衰落,特朗普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税率,成功塑造出美国工人保护者的强硬形象。这一策略不仅稳固了他在中西部摇摆州的支持基础,更成为其执政期间少有的获得广泛认可的政绩之一。尝到政策甜头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将关税手段视为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关税战。他下令对来自185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几乎涵盖了所有贸易伙伴和商品类别。
这场关税风暴初期确实产生了显著效果。欧盟、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等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强烈冲击。为减轻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些国家纷纷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前往华盛顿进行紧急磋商,在多个领域做出让步。特朗普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其强势总统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更加鲜明。然而,这场看似成功的关税行动在法律层面却存在严重缺陷。
特朗普政府为其关税政策辩护时援引了《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但这项法律原本的立法目的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军事冲突等突发性国家安全危机,而非用于处理常规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法律专家普遍认为,这种解释明显牵强附会。今年8月下旬,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比4的投票结果作出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此举属于行政权力越界。面对不利判决,特朗普政府立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法律界对其胜诉前景普遍持保留态度。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对最终胜诉抱有信心,但也承认存在败诉的可能性。一旦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联邦政府将被迫退还约50%已征收的关税,总金额预计在75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这对美国财政将造成巨大冲击——当前联邦财政本就面临预算紧张、国债规模屡创新高的困境,基础设施更新、医疗保障等民生项目的资金已经捉襟见肘。若突然需要退还如此巨额资金,必然导致其他重要领域的支出被迫削减,可能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美国工商界的反对声浪同样不容忽视。汽车制造业首当其冲,福特和通用等巨头因进口零部件关税成本飙升,导致单车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农业领域,由于中国转向采购巴西大豆,美国农场主积压的农产品开始出现霉变,他们强烈要求取消对华农产品关税。零售业和制造业也深受其害,销售中国商品的零售商和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工厂为保持市场竞争力,不得不自行消化增加的成本。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判决政府败诉,这些企业势必会集体要求退还已缴纳的关税,甚至追讨利息损失,届时政府将面临雪崩式的法律诉讼。
国际社会的反应同样值得关注。印度尼西亚已经开始用镍矿资源换取光伏设备,巴西积极推进本币结算贸易,欧盟则明确表示要保持与中国产业链的合作关系。这些迹象表明,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加速调整策略,减少对美国政策的依赖。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政策尤为严厉,不仅将征税范围从第一任期的钢铁、家具等传统商品扩大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还将平均关税税率从10%大幅提升至25%,部分商品在叠加各种名目后实际税率甚至高达104%。这种极端措施明显旨在遏制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然而,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判定这些措施违法,所有加征关税将立即取消,精心设计的黑名单也将失效。更讽刺的是,中国早已将供应链向东南亚和拉美地区转移,而美国企业却要面临失去稳定货源后,不得不接受更高价格或寻找替代供应商的困境,最终受损的反而是美国自身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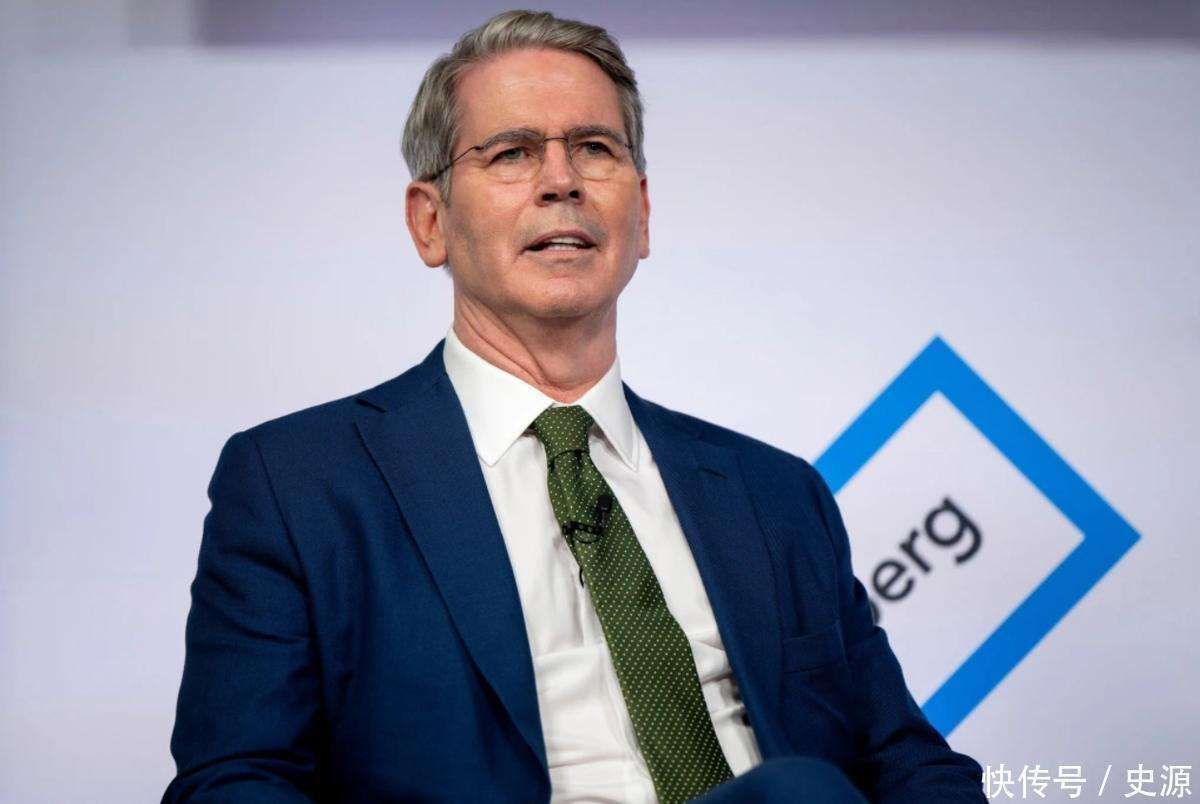
深入分析可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像一把回旋镖,本想打击他国,最终却伤及自身。这一政策不仅使美国陷入巨额退款的财政危机,还导致与传统盟友关系疏远,更意外地推动了中国产业链的加速升级。无论最高法院最终如何裁决,这段历史已经证明: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单边关税作为政策工具已经失效,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只会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孤立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