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狂卖十几亿人民币,这家深圳南山公司成了AI硬件黑马
界面新闻记者 | 梁宝欣
界面新闻编辑 | 林腾
在AI硬件经历激烈分化的2025年,Plaud(深圳机智连接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少数跑通商业化闭环的创业公司。
这家成立不足四年的深圳企业,以AI录音产品为核心切入市场。自2023年6月推出首款卡片式AI录音设备Plaud Note起,产品连续两年保持约十倍增长。截至今年7月23日,Plaud已将产品销往全球170个国家,累计出货量突破100万台。
Plaud联合创始人许高在今年9月的一次公开访谈中提到,2025年的总收入,预计能达到2.5亿美元。这一收入包括硬件产品,以及搭载其上的AI软件Plaud Intelligence。该软件采取年费订阅制,价格区间为99至240美元。
其实,Plaud产品“能卖动”的迹象在早期便显现:众筹期在Kickstarter不到两个月获得超110万美元支持,转至Indiegogo又筹得超238万美元,刷新录音设备品类纪录。借助这两大海外众筹平台完成了需求验证+预售回款,为后续放量铺路。
一位深圳投资人向界面新闻透露,目前Plaud在一级市场上的估值大概是100亿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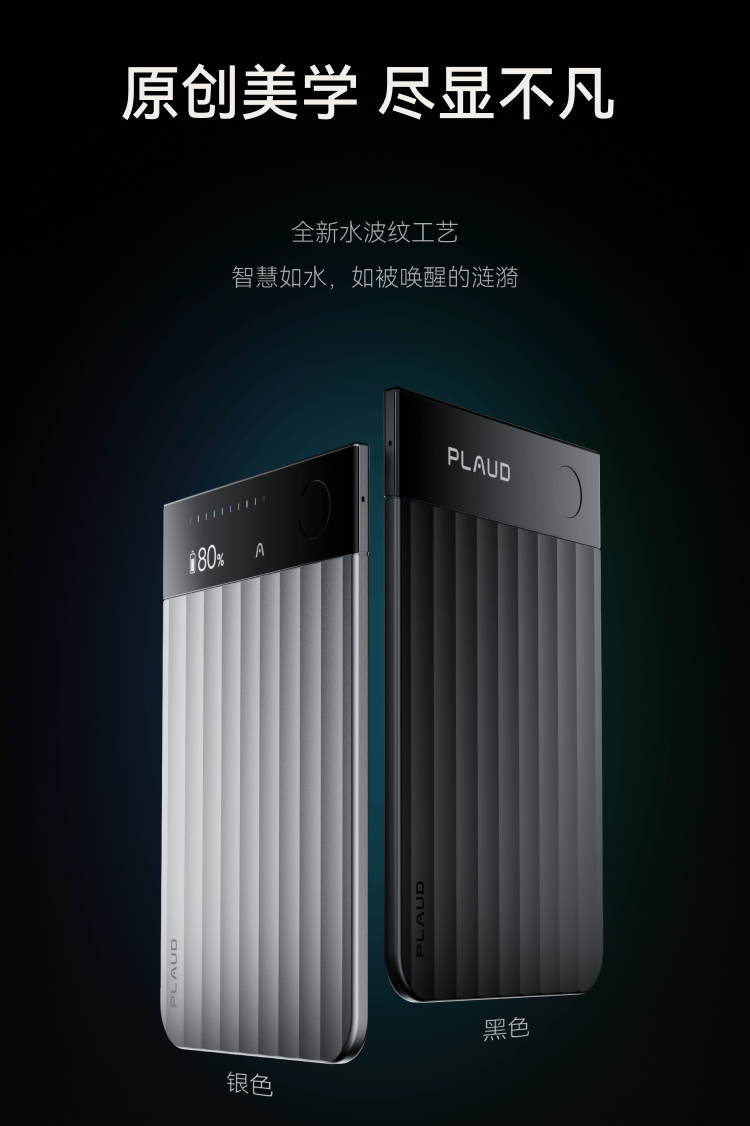
Plaud的首款产品—Plaud note,是一款厚度仅0.29厘米的卡片式录音设备,可磁吸在iPhone背面,支持会议与通话场景下的即时录音,解决了苹果手机无法在通话中录音的痛点。
更关键的是,Plaud是首批将大语言模型引入录音产品的公司。据了解,在推出Plaud note之前,许高曾推出过另一款AI录音笔—iZYREC,这款产品体积比AirPods充电舱还小,但彼时还未有大模型技术支撑,仅能依靠传统自然语言处理(NLP)实现基础转写。
2022年11月,OpenAI推出ChatGPT,这一事件让许高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设想终于具备了现实基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21年,谷歌推出了实时转写APP Live Transcribe,有10亿次下载,但既不保存音频,也不保存文字。
“当时我就想,我们不仅可以做对话的采集、转写、留存,还可以去招NLP的工程师做语义的解析,去抽象会议的主题、会议的要点,会议的总结。”许高说,到了2022年年底大模型出来的那一刻,智能一下子突破了,逻辑就成立了,而且变成一个理论上限很高的东西。
在此背景下,Plaud的第一款产品引入了ChatGPT大模型,实现语音转录、要点提炼与智能摘要等功能,也被业内定义为“全球首款ChatGPT提供支持的录音笔”。
除了抓住了iPhone无法通话录音的痛点和踩中了大模型技术的风口外,不少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早期在海外便快速铺开销售渠道,建立品牌心智,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
生生科技同样在深圳从事AI录音产品研发,但与Plaud不同,其产品更侧重于个人生命记录与日记应用。生生科技创始人刘骁奔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要谈及行业壁垒,Plaud确实具备一定优势。首先,创始人许高具备投资人背景,对市场趋势的判断更为敏锐,较早捕捉到这一细分方向;其次,Plaud在海外渠道铺设投入较早和较广。
“我的合伙人曾在东南亚调研,发现当地不少销售电子硬件的商场里,Plaud的渠道早在过去一两年就已经铺设完成。”刘骁奔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模型尚未形成明确盈利模式的阶段,Plaud以“硬件+软件”组合跑通了AI硬件的商业路径。
目前,Plaud在售的三款主要产品—Plaud Note Pro、Plaud Note 以及 Plaud NotePin S,在京东平台上的售价分别为1599元、1399元和1499元。
在硬件之外,Plaud还建立了配套的会员体系,共分为三档:普通会员、专业会员和卓越会员。其中,专业会员年费339元,卓越会员年费1099元;若用户仅购买硬件设备,则默认为普通会员,每月可转写300小时音频。
付费会员相较普通会员,可解锁全量模板、自定义术语、自定义模板以及“Ask Plaud”等AI增强功能。而专业会员和卓越会员的核心差异在于语音转写时长:专业会员支持每月1200小时转录,卓越会员则为无限时长。
在9月的国内媒体会上,Plaud中国区总裁莫子皓向界面新闻等媒体提到,一个硬件产品如果接入了AI,但用户不愿为AI功能付费,那它几乎无法发挥作用,只能沦为摆设。Plaud从创立之初就将大模型能力视为核心功能,而非附加项。
“我们用的是最贵的大模型,最好的材料和麦克风。”莫子皓坦言,这也使Plaud的产品价格相对更高,但本质问题在于,用户是否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买单。
据界面新闻向业内人士了解,目前国内大模型音频处理的平均成本约为每小时1.24元,包含语音转写、AI分析等API调用费用。对于高频用户而言成本略高,但对普通用户而言,负担不重。“以日均两小时有效录音计算,一个月约30小时,成本在二三十元左右。”该人士认为,这一成本结构为Plaud的订阅模式提供了可持续空间。
在相对可控的成本前提下,Plaud的关键在于能否触达愿意为AI服务持续付费的用户群体。其商业模式的成立,源于对目标用户的精准定位。据Plaud合伙人、全球销售中心负责人孙驰介绍,公司产品的目标用户是“三高”人群,即“高对话依赖、高知识密度、高决策杠杆”。这类用户往往在工作中高度依赖沟通、承担重要决策职责,并且从事知识密集型的职业。其中,企业管理层是典型代表。他们的日常工作以会议、沟通与谈判为主,决策影响范围广、信息密度高,对录音及内容整理的依赖程度也更为显著。
不过,外界也对Plaud的产品价值提出质疑,既然手机能录音,为什么还需要额外的录音设备。对此,许高公开表示,事实上虽然每个人都有强大的手机,但99.999%的人没有在记录,同时手机在收音便利性、续航、交互体验等方面天然存在局限性,从结果上看就是如此。
在海外完成商业验证后,Plaud正尝试将这一模式复制到中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Plaud是一家深圳企业,其发展路径呈现出“出口转内销”特征。产品最初在海外市场销售,随后进入国内市场。
今年9月,Plaud正式进军中国市场。与海外版本相比,国内产品在功能层面保持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底层所采用的大语言模型。
莫子皓表示,公司产品目前已销往全球170个国家,但从未针对任何单一市场进行本地化改动。Plaud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并未对产品功能进行调整——无论是 Plaud Note 还是 NotePin,核心功能保持一致,仅因合规要求在模型层面采用了国内版本。
莫子皓还提到,在中文语言转写方面,国内的模型会比海外的模型更好。而在信息整理等通用能力上,双方差距并不大,大约是三个月的领先。
在他看来,模型差异并不会对产品体验构成实质影响。刘骁奔也表示,大模型接口(API)具有高度开放性,几乎所有硬件厂商都可接入不同供应商的模型,其调用成本差异也不大。“从我的视角来看,对于Plaud的国内市场表现,模型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更大的挑战在于渠道能否快速铺开,以及国内是否存在足够多与海外类似的高净值、强需求用户群。”
此外,在被问及是否对中国市场规模和潜在份额做过测算、以及对Plaud在中国市场的商业表现是否有预期时,孙驰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并没有为中国市场设定具体的份额目标,也没有制定所谓的占比指标。
孙驰提到,在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之前,我们已经进入多个海外市场,其中有些市场与中国颇为相似。例如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职场活跃度高,对AI技术的接受度也较强;更接近的案例是香港,目前Plaud在香港地区每月可实现约两至三千台的销售。由此可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潜力无疑十分可观。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商业表现抱有期待,但同时会保持冷静与克制。”孙驰表示,在内部也明确讨论过“中国区成功的定义”,即用户是否真正认可这款产品。我们不希望陷入低价竞争,更不会以牺牲功能换取所谓性价比。
但中国市场的竞争来得很快。随着Plaud带动这一品类走热,AI录音产品开始吸引大型平台与供应链厂商入局。
“他们已经被钉钉抄底了。”一位深圳AI硬件创业者向界面新闻记者提到。
9月15日,钉钉首款AI硬件产品 DingTalk A1 正式开售。产品同样采用录音卡片形态,通过磁吸方式贴合手机背面,提供青春版(499元)与旗舰版(799元)两种型号。DingTalk A1以“录音+转写+摘要”为核心功能,并与钉钉办公生态深度打通,可实现会议纪要自动转存、生成待办等一键闭环。
与此同时,华强北白牌厂商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能力,将AI录音卡片价格进一步下探至120至150元,迅速占领对价格敏感的下沉市场。
这意味着,Plaud所开辟的赛道正在被快速复制。到目前为止,Plaud的故事,是AI硬件商业化的一次样本。它证明了“硬件体验+模型能力”能够形成真实需求,但同时也揭示了技术红利的短暂性,即模式被验证,竞争便会迅速涌入。
不过,有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提到,Plaud的定位是一家AI公司,并不止于录音产品,而是围绕AI技术寻找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可见,随着钉钉与华强北白牌厂商的加入,Plaud需要讲述的,是一个AI公司的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