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导读:4月26日下文,在清华大学建校114周年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清华MBA名师论道。邀请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清华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教授作《大学的窘境与创新》演讲。
杨斌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清华大学建校以来院系发展的历史,并在校庆之际表达了对前辈教授的敬意,随后与大家分享了著名管理学家、教育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遗作《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基于此书,以“什么是大学?”问题为引,杨斌教授介绍了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分享了全球大学学科设置、管理制度以及发展策略的源起和演进,提出了现代大学正遭遇的“不得不为”的内部窘境和可能“被革新”的外部困境及压力,进而提出“存在是否即是应当”、“一贯如此是否便是理当”的思考题。

01
应然与实然:当 “名校模式” 成为 “生存陷阱”
实然,并不意味着应然,很多时候都是因应使然
“哈佛基因”—— 从择优录取的选拔机制、高额学费与奖学金体系、通识教育与通专融合的培养模式,到荣誉学位制度、终身教职体系、“不发表就走人” 的学术考核机制,再到长暑假、北美校际体育文化、巨量捐赠基金支撑的住宿书院制度等 —— 早已超越个体经验,演化为现代大学的主流特征。
然而当全球高校在“哈佛基因” 的基础上向着“更大更好” 逻辑的发展时,却陷入了 “模仿悖论”:它们既无法像哈佛那样依靠巨额捐赠基金覆盖高成本办学模式(如小班教学、低师生比、豪华校园设施),又因盲目复制名校标配(扩建研究生院、增设热门专业、追求终身教职规模)导致同质化竞争。这种 “一流大学低配版” 的发展路径,最终陷入 “高成本-低认同” 的恶性循环——高额学费推高教育门槛,通识教育与本土需求脱节,学术考核导向偏离教学本质,资源错配让多数高校沦为 “名校影子”,却丢失了自身独特的办学定位。
同时,全球大学排名体系正在强化这一同质化趋势。 当 “排行榜名次” 成为资源获取、生源竞争、社会声誉的核心指标,高校不得不被动纳入 “排名竞赛” 的闭环:为提升国际排名,必须扩大留学生比例、增加英文论文发表、追求 “高显示度” 科研成果,而这些指标与院校服务本土需求、培养应用人才的使命常常产生冲突。这种 “为排名而办学” 的导向,进一步加剧了 “更大更好” 的非理性扩张——新建学院、招聘海归师资、投入硬件建设,最终让排名竞争的内卷也更加剧, “更大更好”的竞赛更无法停下来。
这种将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大学 “实然”发展路径误读为普适性的 “应然”标准是否意味着就该一直这样下去?
大学要有独特性。杨斌教授表示 “办好自己的大学,需要learn,更需要unlearn。 包括从顶尖大学中学习借鉴以及重要的刻意忘却所学;也包括从自己接受教育培养的大学(的一手体验)中学习借鉴、刻意忘却。”在全球有上万所高校,除了顶尖大学之外,占比九成五以上的高校都被新闻报道和研究者长期忽略。这些学校常常会与顶尖大学进行对标。 院校之间,本该是各擅胜场的。综合性巨型大学并非终极模式,动辄就说要服务全世界也难说不是一种使命不清的流弊。院校定位各有千秋,要找准自己的基因,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才有生命力,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达到自己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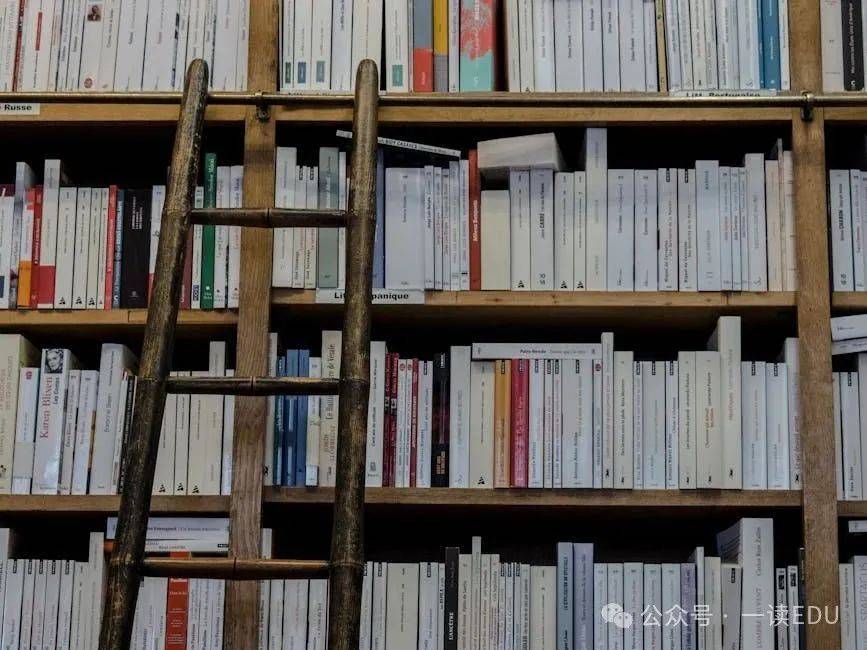
02
与共 各美其美
与共,不能误解为团结,而更强调不同的各主体之间的有机地共生共进,就要看到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多用类思维,少用层级观。
第一种与共,算是比较经典,是否有机会让更多的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从弱势群体能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上获得更多善意与助力?名校能否提供这种机会,不是作秀而是真心认同这对于自身的学习者群体的多样性,对于组织的社会使命,都有内在意义。这是伯克利教授在那场清华分享中着力讲到的,也是包括清华在内的国内各院校都在努力的问题。虽然问题经典,但不好说都有了可靠的解法,也还怕会遭遇反复。
另一种与共,是否更大范围、更多元多样、不同类别的高等院校都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是否正走在追求独特性、贴近社会和人民需求的办出特色的路上?这一种与共,强调的是名校与普校之间的与共。高等教育真得是要建设共同体,百花共美。这里,恐怕我们要对什么是花、怎么才美有更广泛也更深刻的理解。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常被引为励志典范。但“学”字背后是模仿逻辑,苔花何须学牡丹?它本应有自己的绽放方式。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中,“美人之美”,讲的是牡丹看到苔花,要懂得苔花特殊的美,而“各美其美”鼓励苔花自己也要对自己的美有自信,这才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学牡丹,不好,要竞自由,竞相开放,苔花就要开出与牡丹不同的美好来,也会有更喜欢苔花的欣赏者去求去爱,这才建构出一个参差多态、各有其福的生态系统。
第三种与共,是实体校园与线上和各种新技术进化后的教育形式的与共发展。一方面,要理解技术的迭代逻辑,是越多人用就越有机会更快迭代到更好,也会在成本和可及性上从“重器”进到“众器”,走入寻常百姓家并更易上手。另一方面,不管在线也好,人工智能也罢,新技术来了,与传统教育中的很多角色,不是谁要替代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融合升华形成一个新事物,新形态。“替代论”、消亡论调,真的是故意吸引眼球的惊人之语,造成的影响还很大。这些对立观没有含“智”量,不值得评论,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积极推动技术与人的融合,让与共而生的新生命体来彻底消除“替代论”的市场。
不妨设想一下,或许未来取得高等教育学位的方式,包括有资格授予学位的机构,应该会也必须要更加多元丰富(比如公司企业)。如果仍囿于封闭保守,那么完全不能排除,我们近几十年熟悉的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被瓦解或至少对经济和社会变得不那么重要(irrelevant)。
当每一所大学都能在 “learn” 中吸收养分,在 “unlearn” 中摆脱桎梏,在 “与共” 中找到坐标,高等教育才能超越 “排名竞赛” 的迷途,抵达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本真境界——这才是大学应有的生命力。
最后,将杨斌教授的思考问题留给您“What is Ignored by the Media...... but Will be Studied by Historians?”欢迎您留言,参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