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的失格 从协和的董袭莹到上戏那尔那茜再到武大的杨景媛,看名校的戏剧面孔
近日,几幕高校舞台上的荒诞剧令人瞠目:从协和医院董袭莹的“钉子户般的傲慢”,到上海戏剧学院那尔那茜的“风轻云淡”,再到武汉大学杨景媛的“飞扬跋扈”——这些碎片,折射出的不仅是某些个体的失范,更是高悬于象牙塔顶端的制度与精神的全面塌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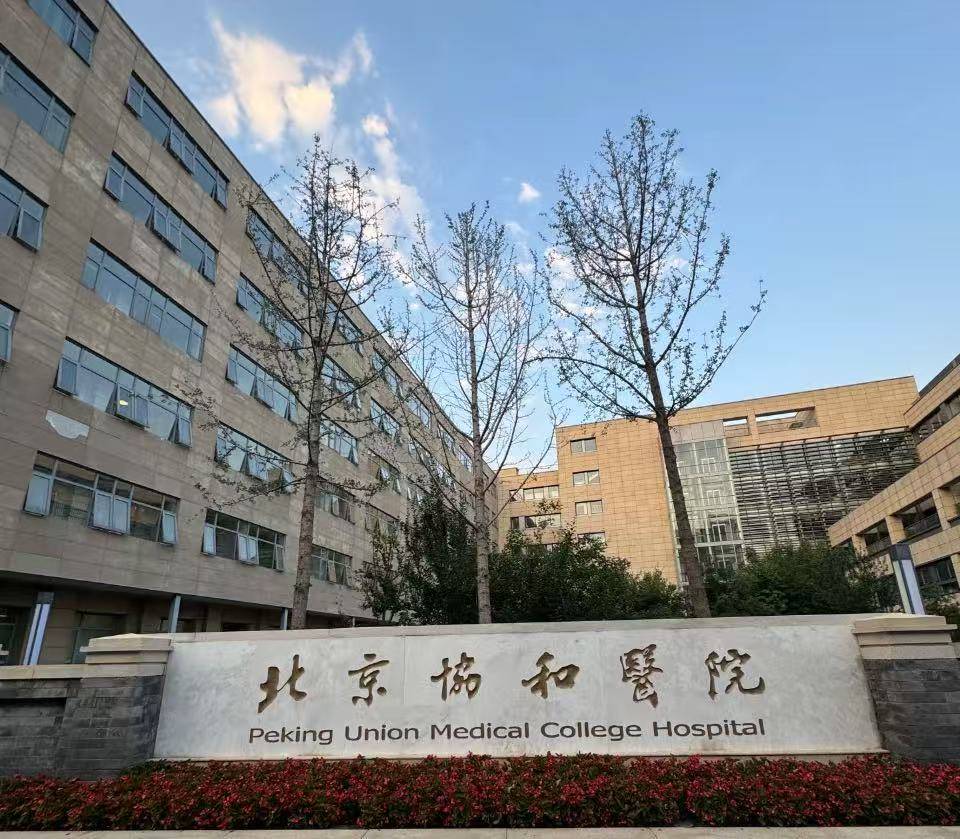
当高校招生机制沦为“旋转门”,特权便堂皇登场。本应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在部分角落却异化为寻租的暗渠。从董袭莹、那尔那茜到杨景媛事件,无不将矛头指向招生流程中那难以言说的“操作空间”;面对汹涌质疑,要么是校方沉默,要么是等上级领导安排的回应更令人齿寒——它无异于宣告,所谓规则在“背景”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当特批通道成为VIP包厢,当程序正义沦为遮羞布,寒门学子仰望星空的窗口,便被无形之手悄然关闭了半扇。

“名校风骨”这一昔日荣光,如今竟成了某些学府身上最刺眼的讽刺。面对质疑,一些名校的应对之道竟是:回避、沉默,甚或变相袒护。面对舆情何尝不是一种对公义的傲慢轻慢?这背后,是对学术圣殿声誉的漠视,更是对公众信任的无情挥霍。当守护殿堂者开始亲手拆解殿堂的基石,名校的光环便只能照亮虚空。

最为彻骨的悲凉,莫过于知识精英脊梁的集体软化。人们曾期待大学教授、校长们成为社会的良心与标杆。可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面对不公时的集体噤声,甚至对不义现象的暧昧默许。当杨景媛们可以“飞扬跋扈”,当董袭莹们被指“傲慢”却仍稳坐钓鱼台,背后折射的,是监管的形同虚设,更是部分师者道德勇气的缺席。知识分子的膝盖,竟比普通人更软——这真是时代最深的悲哀。
象牙塔的失格,是制度之殇、名校之耻,更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陷落。当神圣的学术殿堂也飘荡起特权与傲慢的尘埃,当肩负社会期许的学人脊梁开始弯曲——我们失去的,又岂止是招生的公平?
未名湖的水再深,映不出博雅塔真正的倒影;珞珈山的樱花再盛,也掩盖不了某些角落的腐土气息。重建之路,唯有从刮骨疗毒的勇气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