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的12岁“天才少年”
潮新闻客户端 实习生 何熙 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李彬
他上课不听讲,却能自学成才,韦氏智力测试高达145,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是老师眼中的“小天才”。可在家里,他总在家庭聚会时自顾自玩游戏,与同学也频频爆发冲突,因为与他人相处困难而陷入迷茫失落,还出现过激攻击行为,在父母眼里是个难以捉摸的“怪咖”。
这是12岁初一学生小宇身上呈现的矛盾图景,而解开这一谜团,他与家人足足经历了两年曲折的就医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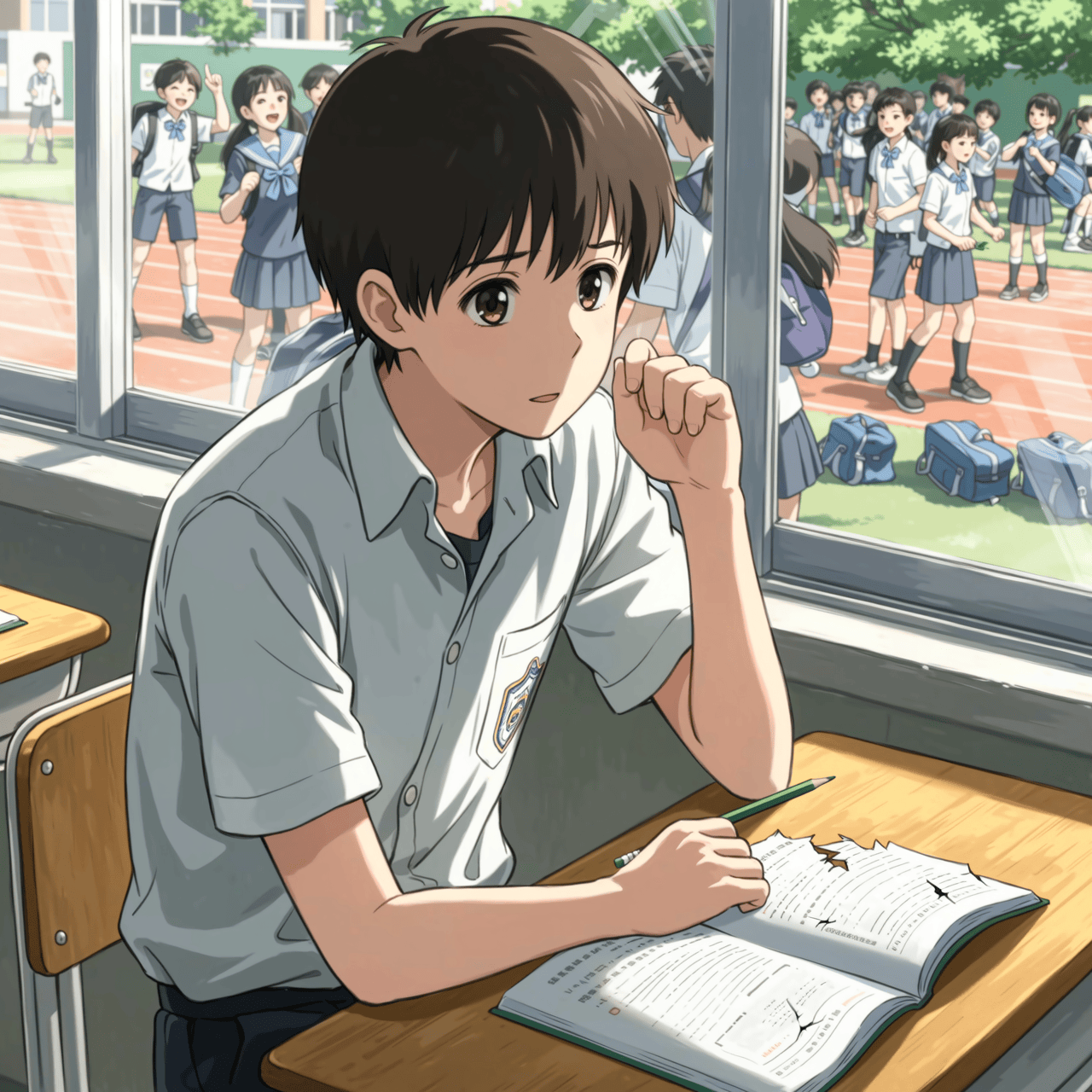
照片由创作大脑AI生成
四次就医:精准诊断的艰难跋涉
小宇的就医历程始于10岁,彼时父母带着他走进综合医院心理科,告诉医生“孩子叛逆、厌学、沉迷网络”。
问诊时,小宇因为极度焦虑和表达困难表现得沉默抗拒,父母不断强调孩子“不听话”“逃避现实”。最终医生诊断小宇为“童年情绪障碍”和“网络成瘾”,建议家庭加强管教、限制网络使用。可这一建议却激化了家庭矛盾,父母收走电脑手机后,小宇出现了强烈的情绪崩溃与自伤行为。
11岁时,小宇因注意力无法集中,家人怀疑他患有多动症(ADHD),遂带其前往神经内科就诊。经过常规检查,未发现小宇存在器质性病变,医生判断其注意力问题源于情绪,而非ADHD,建议转回精神科。
直到12岁,小宇来到浙大精中(杭州七院)儿童心理科专科门诊,事情才迎来了转机。接诊医生在聆听漫长病史后,敏锐捕捉到“痴迷系统性知识”“无法理解社交”“语言缺乏情感交流”“刻板行为”一系列关键信息。为进一步明确情况,医生单独与小宇父母及小宇本人进行了长时间访谈,细致追溯了小宇从婴幼儿期至今的发展历程,同时通过游戏互动观察了小宇的社交反应、沟通方式、兴趣及行为模式,还运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2)、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等工具开展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小宇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存在显著差异,在积木、常识等领域表现出色,理解社交情境方面分数却极低。结合其成长经历——婴儿期喂养睡眠规律,言语、运动发展早于同龄人,1岁开始说话且词汇量积累快,但2岁后语言出现“质”的异常,像“小大人”般能背诵大量古诗、广告词甚至乐谱,交流时却常不合时宜;热衷谈论天文、地铁线路图等自身感兴趣的话题,不顾及对方感受,无法进行双向对话;对风扇、洗衣机等旋转物体极度痴迷,后期又沉迷研究行星排列和交通系统;出行要走固定路线、穿固定衣服,物品摆放位置不能变,否则会极度焦虑哭闹;幼儿园时看不懂同伴脸色与玩笑被孤立,对吹风机、吸尘器声音敏感,吃饭只吃米饭和土豆,小学时不遵守纪律、课堂突然大笑、要求同学体育课必穿运动鞋等——医生最终明确诊断小宇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且共病抑郁症。
“小宇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叛逆或抑郁,核心在于他大脑处理社交信息和感官信息的方式与常人不同。他过去的种种‘问题行为’,都是在用自己有限的方式应对让他困惑且信息超载的世界,长期的误解和缺乏支持,最终导致了抑郁情绪。”医生的这番解释,让小宇家人豁然开朗。
诊断之后:转变干预方向,直面未来挑战
得知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小宇的父母泪流满面,这泪水并非源于悲伤,而是长久困惑后的释然。他们终于明白,孩子不是“坏”,只是“不同”。而对小宇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获得一个能够解释他所有痛苦的框架。他感慨道:“原来我不是一个故障的地球人,只是一个运转正常的火星人。”
此后,小宇一家的干预方向发生了彻底转变。在心理教育层面,全家人开始共同学习阿斯伯格综合征相关知识,调整与小宇的互动模式,不再强迫他“合群”,而是尊重他对天文等领域的特殊兴趣,并鼓励他深入研究,将兴趣发展为优势;在支持重心上,从过去的“矫正行为”转向“提供支持”,不仅为小宇申请学业调整,还帮助他学习社交技巧策略;同时,针对小宇的抑郁症持续开展治疗与管理。
然而,诊断带来希望的同时,挑战依然严峻。小宇需要弥补多年来缺失的社交技能,处理过往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更要在一个为普通人群设计的社会中,艰难探索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医生表示,小宇的案例是众多阿斯伯格综合征患儿家庭的缩影。这类患儿就医之路往往曲折,一方面是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早期语言和认知能力通常正常,甚至超常,容易掩盖核心的社交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常伴随焦虑、情绪问题、感官敏感等共病症状,这些症状往往成为首要主诉,导致被误诊为其他疾病;此外,非专科医生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尤其是高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可能缺乏足够的识别能力。
在此,医生提醒,若发现儿童表现出社交困难、沟通模式奇特、行为刻板且伴有强烈特殊兴趣等情况,应尽早带孩子前往发育行为儿科或儿童心理科进行专科评估,让孩子及时获得精准诊断与有效支持,为他们的未来点亮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