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在十年前达到巅峰,它是原因之一
Nose
《毒枭》这部剧,也有十年了,当年我是很喜欢的,不过,时隔多年重看,还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因为它早已超越了一部普通犯罪剧集的范畴。
从产业角度来看,这部剧集是跨国电视制作模式的一次关键性演进,它完善并输出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型。

《毒枭》
这部剧播出这么多年来,围绕它有许多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对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人物塑造,或者关于这个人物准确性的辩论,却往往忽略了这部剧创新的核心。
核心问题并非《毒枭》讲述了什么故事,而是它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以及它究竟是为谁而讲的。
《毒枭》的诞生,恰逢「电视黄金时代」的巅峰。
以《绝命毒师》《黑道家族》和《火线》为代表的「品质剧」已经成功培养了全球观众对道德模糊、性格复杂的反英雄主角的浓厚兴趣。

《火线》
观众不再满足于非黑即白的善恶对立,而是渴望探索人性的灰色地带。
《毒枭》切入了这一潮流,但它巧妙地将叙事重心从纯粹的个人心理沉沦,就像《绝命毒师》那样,转向了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博弈。
与此同时,2010年代见证了真实犯罪题材的爆炸性复兴。诸如《制造杀人犯》和《纽约灾星》等纪录片剧集风靡一时,反映出观众对「基于事实」叙事抱有强烈的信任与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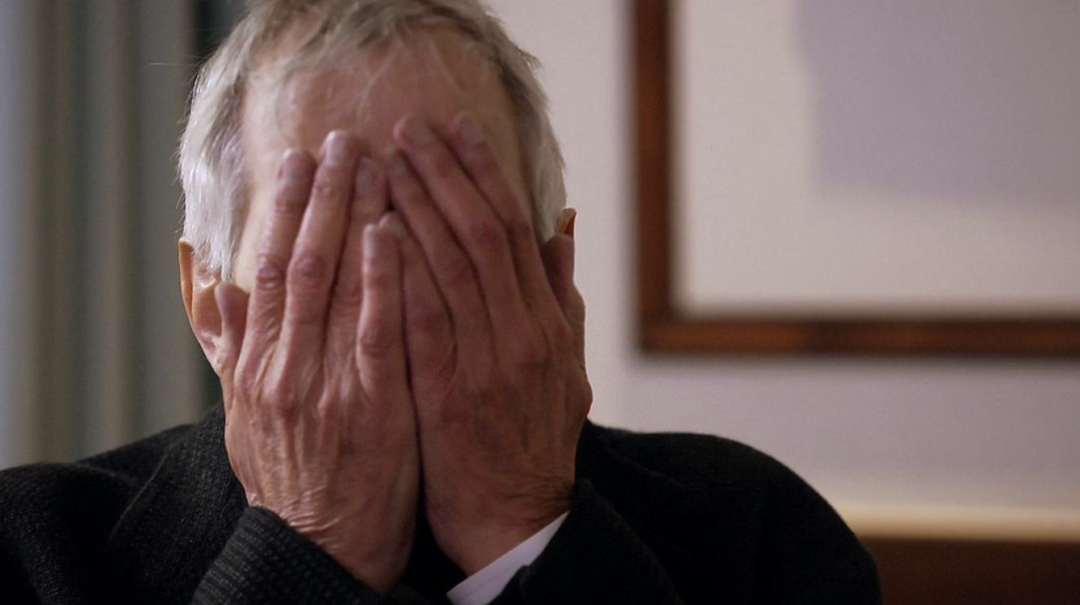
《纽约灾星》
《毒枭》的创作团队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开创性地将品质剧的高制作水准与纪录片格式所暗示的客观性融为一体。这种类型融合,不仅满足了观众对戏剧冲突的期待,也迎合了他们对探寻历史真相的渴望。
更为关键的是,Netflix作为播出平台,它的规则也极大地塑造了《毒枭》的叙事形态。Netflix推广的「刷剧」模式,允许观众一次性观看整季内容,这颠覆了过去的一周一集的「追剧」模式。

《毒枭》
新的模式为信息密集的叙事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一个在传统周播模式下可能因复杂性而显得晦涩、劝退观众的故事,在「刷剧」文化中反而变得极具成瘾性。
观众可以用短时间彻底沉浸在剧集构建的世界中,消化它庞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这种观看体验本身就强化了剧集的吸引力。
2015年前后,Netflix正处于历史上最激进的全球扩张阶段。公司的美国本土市场增长开始放缓,向国际市场进军成为其维持增长、实现盈利目标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Netflix大举进入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数十个新市场,迫切需要能够跨越文化壁垒、连接其既有美国用户基础与新兴国际观众的内容产品。
《毒枭》正是Netflix跨国内容战略的典范之作。该战略的核心是打造「本土故事,全球吸引力」的内容。

《毒枭》践行了这一理念:它讲述一个哥伦比亚的故事,在当地实景拍摄,并大量使用西班牙语对白,这赋予了剧集一种异域的真实感;但与此同时,它通过美国缉毒局(DEA)探员的视角和旁白来构建整个故事框架,确保了其核心的美国市场观众能够轻松理解和代入。
这种双语并行的结构并非单纯的美学追求,而是一项经过精密计算的商业策略,旨在用一个「本土化」的外壳包装一个「全球化」(也就是美国化)的内核。
该剧的创作者何塞·帕迪利亚和埃里克·纽曼最初向Netflix兜售的构想,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史诗——「可卡因的历史」。

他们计划用数季的篇幅,追溯从哥伦比亚麦德林,到墨西哥锡那罗亚的整个毒品贸易链条。
这种宏大、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野心,与Netflix基于数据的运营模式不谋而合。Netflix偏爱能够构建庞大世界观、可持续开发多季乃至衍生剧(如后来的《毒枭:墨西哥》)的长篇内容。
因此,《毒枭》的混合形态,我想称之为「纪实性帝国主义」,这不仅是一种创作选择,更是解决Netflix商业难题的战略方案。
「纪实性帝国主义」是通过一系列精密的美学技术得以实现的。
《毒枭》的叙事配方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画外音、档案影像,和视觉风格。它们相互协作,共同构建了一个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叙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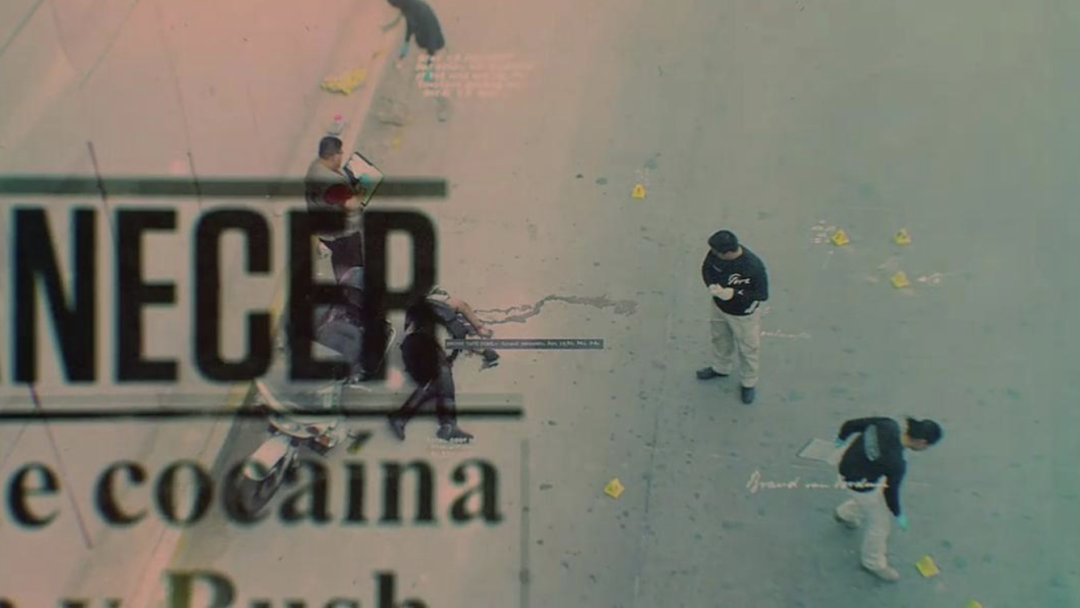
《毒枭》最核心的叙事装置,无疑是DEA探员史蒂夫·墨菲贯穿始终的画外音旁白。「美国佬」的声音,成为了观众进入哥伦比亚那个混乱世界的向导。

它不厌其烦地为观众「翻译」和「解释」哥伦比亚的文化、政治,甚至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简化为一难以置信」的奇观加以介绍。
这种设定,从根本上将美国的视角确立为理性的、默认的观察基准,而哥伦比亚发生的一切则被置于被审视、被解读的他者位置。
墨菲的旁白语言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暗示。他那副愤世嫉俗、见怪不怪的口吻,将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描绘成一种应对「南方」问题的、虽不完美却必要的回应。
尽管旁白表面上承认了道德的灰色地带,例如「好人中的坏人和坏人中的坏人……以及灰色地带的人」,但其底层逻辑始终将冲突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

在技术层面,剧集的混音处理刻意将旁白音量调得比其他音轨更高,这在听觉上进一步强化了旁白者的主导地位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然而,这位看似全知的叙述者,实际上是一位极不可靠的历史学家。
作为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墨菲的立场带有显而易见的偏见,但剧集却将其个人化的回忆包装成了客观的历史记录。
这正是「纪实性帝国主义」的核心机制:将一个高度主观的视点,嵌入到一个暗示着客观与真实的框架之中,从而巧妙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灌输。
为了进一步强化其叙事的「真实感」,《毒枭》无缝地将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包括新闻片段、历史照片,其中一些甚至来自埃斯科瓦尔的私人摄影师,还有政府文件,编织进戏剧化的叙事中。

《毒枭》第二季
这种手法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现实效应」,使得虚构的场景获得了本不属于它的、源自历史事实的权威性。
有一个评论是,「现实不断地打断虚构」,非常准确。这种打断非但没有造成疏离,反而让观众更加确信他们所见即为真实。
然而,这些档案资料的选择,是经过高度筛选和精心编排的。剧集倾向于使用那些能够凸显哥伦比亚暴力与混乱的影像,这在无形中加深了对该国的刻板印象。
同时,剧集也频繁插入强调美国政治回应的片段,例如罗纳德·里根总统夫妇发起的「就说不」反毒品运动的宣传片。这种选择性的呈现,与旁白所建立的叙事框架,形成了完美的互文关系:旁白为你解释事件的意义,而档案影像则「证明」这些解释的真实性。

《毒枭》
图像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文化编码。
在观众的认知中,粗糙、带有颗粒感的黑白或旧式彩色影像,本身就带有一种「真实」的光环。
当剧中由演员扮演的埃斯科瓦尔的画面,与埃斯科瓦尔本人的真实入狱照紧密衔接时,再现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便开始消解。
观众被引导着去相信,整个剧集所呈现的叙事,都如同这些档案片段一样,是确凿无疑的历史。
于是,虚构被现实所认证,而现实又被虚构所诠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强化的叙事循环。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毒枭》的表征政治,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学术概念——拉丁主义。这一概念脱胎于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指的是一套将拉丁美洲建构为「他者」的表征系统。
在这套系统中,拉丁美洲被描绘成充满异域风情、暴力、腐败、非理性和原始落后的地方,而这种描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向定义并提升一个优越的、理性的、现代的美国/西方自我身份。
《毒枭》的视觉语言,正是「拉丁主义」的完美实践。
首先,在色彩运用上,剧集普遍采用饱和度极高的黄色或橙色滤镜,来营造一种所谓的「西班牙裔毒品圈氛围」。

这种处理在视觉上将哥伦比亚编码为一个炎热、危险、充满异国情调的空间,与剧中未经这种调色的、呈现为「正常」状态的美国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在场面调度上,剧集不断重复展现哥伦比亚作为一个充斥着贫困、腐败和暴力的国度,生命在这里显得廉价而脆弱。
这完全符合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刻板想象。更有甚者,在镜头构图上,美国角色(如墨菲)常常被置于画面的「特权区域」,姿态充满主导性,而哥伦比亚角色则被边缘化,或呈现出顺从、无奈的身体语言。

剧集的情节设计同样在不断强化「拉丁主义」的陈词滥调。埃斯科瓦尔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土匪」形象:他充满大男子主义气概,时而残暴时而慷慨,但最终在组织和策略上显得混乱且无能,需要美国的介入才能被制服。
哥伦比亚的政府和军队则被描绘成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没有美国的指导和援助便寸步难行。而剧中的拉丁女性角色,则往往被简化为利用性感来换取权力的工具,进一步固化了对拉丁女性的刻板印象。
这三个核心美学元素——旁白、档案和视觉风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紧密咬合的叙事控制系统。
旁白告诉你该如何思考,档案「证明」这是真实的,而视觉风格则让你从感官上「体验」到这种被建构出的文化差异。
这便是「纪实性帝国主义」的引擎,它以一种极其高效且不易察觉的方式,完成了其意识形态的传播。

在《毒枭》诞生之前,《绝命毒师》已然是犯罪题材剧集的巅峰之作。
两部剧集都围绕着一位崛起的毒枭展开,但它们的叙事根基和意识形态功能却截然不同。
《绝命毒师》是一个纯粹的虚构故事,它深入一个普通人道德沉沦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一场浮士德式的心理悲剧探索。而《毒枭》则宣称自己是一部历史史诗,它讲述的不是个人的堕落,而是一堂关于地缘政治的「公开课」。
这种差异导致了两部剧集在复杂性呈现上的根本不同。《绝命毒师》的复杂性是向内的,它聚焦于沃尔特·怀特内心善与恶的激烈交战。而《毒枭》的复杂性是向外的,它描绘了一个由贩毒集团、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构成的庞大网络。

《绝命毒师》
因此,《绝命毒师》邀请观众对主角产生共情,去理解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挣扎;而《毒枭》尽管也展现了埃斯科瓦尔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温情一面,但最终,通过美国叙述者的视角,他始终是一个被分析、被审视的异类样本,观众与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安全的审视距离。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凝视」的方向。《绝命毒师》的叙事视角深植于罪犯的世界内部,而《毒枭》的视角则源自追捕他的执法者。这一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彻底改变了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于全球大多数观众而言,《毒枭》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娱乐盛宴;但对于许多哥伦比亚人来说,它是一次对国家创伤史的粗暴重述和商业利用。

《毒枭》
哥伦比亚观众对这部剧的负面反应,并非简单的吹毛求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抵抗。他们反抗的,是被他者定义自身历史的权力不对等。正如一位当地人所言:「我已经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了,我不需要再经历一次。」
哥伦比亚观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这些批评共同揭示了「纪实性帝国主义」叙事,在遭遇拥有真实历史记忆的观众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
首先是语言的失败,剧中主演瓦格纳·马拉的巴西口音,以及其他来自泛拉美地区的演员无法准确模仿麦德林地区独特的「派萨」方言,是哥伦比亚观众最常诟病的一点。

这并非小题大做。口音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埃斯科瓦尔之所以能在麦德林底层民众中获得某种罗宾汉式的支持,与他地道的本土身份密不可分。一个说着巴西口音的埃斯科瓦尔,不仅在听感上造成了巨大的疏离,更象征着创作者对文化特殊性的漠视,仿佛整个拉丁美洲可以被视为一个同质化的、可互换的文化符号。
剧集将DEA探员墨菲和潘那塑造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英雄,而大量真正在反抗埃斯科瓦尔斗争中牺牲的哥伦比亚记者、政治家、法官和警察,却被边缘化甚至完全抹去。这种叙事选择,是「纪实性帝国主义」框架的直接后果。它必须将美国的干预合理化、英雄化,即便这意味着要扭曲历史,将本属于哥伦比亚人的抗争功绩归于美国特工。
许多哥伦比亚人认为,该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进一步固化了国际社会对哥伦比亚的负面印象,即一个只与可卡因、暴力和腐败相关的国家。
它利用了哥伦比亚人急于摆脱的悲惨过去来牟利,这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剥削。在他们看来,这部剧是一场针对哥伦比亚的滑稽模仿秀。

为了追求戏剧效果,《毒枭》对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和虚构。埃斯科瓦尔的儿子塞巴斯蒂安·马罗金曾公开列举了剧中28处与事实不符的情节。这些「错误」并非无伤大雅的艺术加工,它们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叙事目的,即简化复杂的历史,塑造更符合好莱坞戏剧逻辑的人物关系和事件。
2015年,与《毒枭》同年问世的还有一部重要的电影——《边境杀手》。两部作品都以美洲的禁毒战争为题材,却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批判。

《边境杀手》
《毒枭》所呈现的道德模糊,最终导向了一种「必要之恶」的结论:好人为了打败更坏的坏人,不得不弄脏自己的手。这是一种为美国干预主义辩护的实用主义逻辑。
相比之下,《边境杀手》则展现了一种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和制度批判。它揭示了所谓的「禁毒战争」并非为了胜利,而是为了建立秩序,即控制毒品流动的渠道和利润,使其处于美国可以管理的范围之内。
在这部电影中,美国的干预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一个自我延续、不断制造更多暴力的腐败循环。
两部作品对观众引导者的选择,也体现了它们意识形态的根本分野。
在《毒枭》中,我们的向导是深谙内幕、愤世嫉俗的「圈内人」墨菲。而在《边境杀手》中,向导则是天真、理想主义的「局外人」——艾米莉·布朗特饰演的FBI探员凯特。

《边境杀手》
观众通过凯特的双眼,体验到这场影子战争的恐怖、荒诞与道德迷失。《毒枭》最终让观众理解并接受了这套体系的运作逻辑,而《边境杀手》则让观众从根本上质疑并唾弃这套体系。前者是对体系的辩护,后者则是对体系的控诉。
所以在我看来,《毒枭》最核心的创新,是它成功地完善了「纪实性帝国主义」这一叙事模式。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特定的地缘政治观点,包装成可供全球观众「刷剧」的、极具吸引力的娱乐产品。

《毒枭》
《毒枭》后来成为了Netflix乃至整个流媒体行业都采用的成功模板,也就是寻找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从一个美国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讲述,并大量运用纪录片的美学元素,为其赋予不容置疑的「真实」权威。
这个模式是高效的、可扩展的,《毒枭:墨西哥》《末代沙皇》的后续成功便是明证。
其他例子还包括,HBO的《切尔诺贝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谈这部剧,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