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网红大撤退:下坠的电商,过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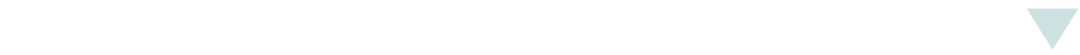
11月初,杭州萧山,丽晶国际。
这是一栋近30 万平方的超大单体建筑,也是中国网红直播行业的象征。媒体如此形容它曾经的盛况:“活跃着近2万名主播和打工人,创下的GDP相当于一个镇。”无数初入行的年轻人,把它当作“杭漂第一站”。
正值2025年双十一如火如荼之际,这个符号性建筑却显得有些冷清。走进星级酒店般的大门,大理石装饰的金色大堂两侧,都设置了生人勿近的闸机。早上10点,等电梯的人不多,不复鼎盛时期挤到“等十分钟是常事”的景象。出入的住户衣着入时,多牵着狗,言语间很少谈论直播、数据或销量。
“早些年,网红都住这边,”一位房产中介介绍道,“现在住的也有,但主要做个人拍摄,没有大型直播间了。”丽晶国际的LOFT户型能商住两用,上楼睡觉、下楼直播,2019年前后,曾是四季青服装档口老板们的首选。
现在,房东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一居室的租金从三千多降到了两千出头,即便如此,还有房东在网上发问:空了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今年这么难租?据丽晶楼下的房屋出租告示牌显示,至少有50套房源空房以待,正在登记招租,而在安居客上,这一数字是147套。这个网红楼盘的沉寂,似乎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陨落。
这样的退潮不止于丽晶国际。今年4月,辛选从杭州滨江撤离,搬回广州,曾经灯火通明的海威中心3号楼已人去楼空,楼下的星巴克也因失去客源关门;港圈豪门的向太也退租了在滨江花重金打造的办公楼“智慧之门”;“疯狂小杨哥”则在同一时间离开了滨江的博地中心;杭州写字楼空置率在今年第二季度创历史新高,达到27.7%……
于是,这一年坊间盛传:杭州网红正在大撤退。
的确,直播的淘金时代过去了,伴随直播间流量和销量下滑,主播们的收入也在集体缩水,那些自认以命换钱、但月入3万愈发困难的人们正在考虑转行;电商老板们也被套牢在巨额库存和居高不下的退货率上,渴望天降流量起死回生;双十一前夕落地的“电商税”,更是可能成为压死“刷单玩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应届生主播们涌入,接受越来越低的薪资,行业也越来越卷了。
但我们接触的四位直播从业人员,无论前主播还是策划、运营、商务,他们坚持认为:杭州仍是直播行业的天花板,留在这里继续做网红直播或是周边工作,仍然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兜兜转转,不少人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城市,继续寻觅下一个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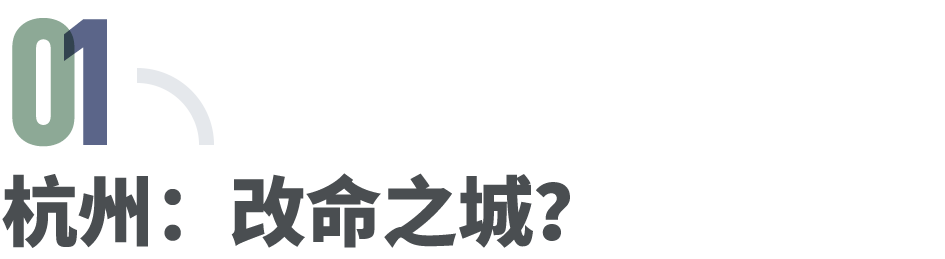
从丽晶国际的阳台望出去,钱塘江、亚运村可尽收眼底。这里属于杭州的头部板块之一,交通便利,附近聚集着诸多直播机构:薇娅的谦寻、罗永浩的交个朋友、号称“宇宙第一MCN”的无忧传媒……
吃饭时间,随意走进一家丽晶国际附近的餐馆,还是能高频碰到网红主播。路过美甲店,也能看到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的女孩,在为下一场开播烘干甲片。通过美貌,你很容易将她们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李雯在杭州的头部MCN机构遥望科技,做过直播策划,“我们公司的所有主播,不管能力怎么样,至少看上去是美女,是介于普通人和明星之间那一层的人”。在杭州,努力很重要,但颜值是门槛。后来她去了广州,她感觉,广州主播“更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普通人努努力也能当主播,对于颜值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 丽晶国际楼下至少50套房源空房以待
刘惠住在离丽晶国际不远的小区。三年前,做主播的朋友介绍她来杭州,说这里“赚得多”。大学毕业后,刘惠在长沙做了三年综艺后期,一开始是零工资,每月只有餐补300元,“那几年只吃到了苦,钱根本没赚到”。后来,她把杭州称作“改命的城市”。
来杭州后,她在辛选做短视频剪辑。今年4月份,她跟着公司搬去了广州,之后,部门裁员,她所在的那层楼,连同保洁阿姨,所有人都被裁了。她没多想,很快搬回了杭州,“同样的剪辑岗位,广州的工资至少要比杭州少三千块钱”。
刘惠老家在辽宁沈阳,背井离乡的唯一目的是挣钱:“我可能工作到35岁左右,赚到目标的钱,就回老家养老。”在东北,以大连举例,编拍剪全做,工资可能也就2400元左右;但在杭州,28岁的她可以轻松月入过万。
过去七年,在杭州滨江,许多年轻人抱着和刘惠相似渴望“改命”的心态。刘惠的主播朋友,2021年来到杭州,那时候,直播电商行业还在迅速发展,只要愿意做,没经验的小白也有工作机会,靠打工,三四年攒够一百万没问题。在短视频平台上,靠自己的能力买宝马、小米SU7,是最时髦的大女主人生。
李雯还记得,2022年她刚来杭州,公司还在大量扩招直播方面的人才:共计1400多名员工,1200多人都在直播团队。做直播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做综艺的,做品牌的,也有像她这样,原来在北京从事音乐行业的。来杭州后,她觉得生活比北京“赶”多了:一整个月她都在加班,凌晨两点下班,早上十点又出门上班,忙起来的时候连大小周也没有。“可能大家都急着在年轻的时候把钱赚了,”她说,当时,一个月拿两三万的人很多,“普通人凭本事拿到高工资,大家都很有冲劲。”
直播间里,李雯每天都在面对金钱数字的冲击。刚入行的时候,一晚上成交额100万也让她“觉得很夸张”,时间久了,卖1000万,也很难让她感到兴奋。在这种“搞钱”的氛围下,每年618、双十一,甚至团建,公司都会组织团队,去西湖灵隐寺的财神庙拜一拜。
“杭州人赚钱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李雯说,“他们喜欢交流,也敢做。”李雯的老板,遥望科技的CEO谢如栋,在2018年看到了直播电商的商机:这一年,散打哥在快手直播10小时带货1.6亿,在淘宝崭露头角的李佳琦则凭借“OMG,买它!”成功出圈。谢如栋“非常震惊”,之后他把公司的办公室都改成了直播间,找明星合作带货。
谢如栋没有赌错。直播电商后来创造的财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巅峰时期,李佳琦在2022年双十一预售首日,创造了215亿的惊人交易额。网红带火了钱塘江两岸的大平层。2020年薇娅买下四套嘉润公馆,时值3500万元。

◎ 丽晶国际的阳台视野

如今,薇娅因为税务处罚退居幕后四年,辛巴也在今年8月称,因肺部患严重疾病永久退出直播行业,仍活跃的李佳琦直播间,也是平平淡淡地卖货,热闹不复往年。头部主播尚且倦怠,小主播就更难熬到出头之日了。
今年,刘惠的主播朋友打算回东北老家。等租的房子到期就走,她“太累了”,行情也不好,一直在降薪。过去她时薪160元,一天播4小时,赚五六百块钱没问题。现在,主播太多,时薪腰斩到80元都有人抢着干。
杭漂三年的程星瞳则已经在年初回了山东老家。临走前,她观察到:B级以下的主播都不是很好找工作了——在主播行业,B级主播指时薪300元以下的普通主播;“可替代性很强,在那种单品直播间,背熟了话术,加上一些镜头表现力就很容易上手,现在,大批量的‘廉价’大学生涌入直播行业,淘汰掉了这些主播。”程星瞳说。一些新人主播还面临公司给低薪却要求播6小时的情况,“我觉得纯属是‘招黑奴’,不把主播当人了”。但S级主播,时薪在500元以上的,能跨多品类、有控场能力的,程星瞳认为,还有生存空间。
程星瞳今年31 岁。2023年来杭州时,她的第一份主播工作是卖女装,底薪8000元,无提成。之后一年多里,她换了五家公司,底薪递涨,到最后一份工作,旺季时,她一个月已经能赚十多万了。“临走前我是不缺市场的,但身体真的受不了了。”她说。
在杭州,她的工作节奏通常是这样:上班,播女装,穿高跟鞋,每场过一两百件衣服,复盘,下班。每天4小时播了半年,有段时间她感觉自己“已经虚得快死了”。
“审问犯人的时候有一种刑罚:在犯人面前照一排灯,用强光刺激他,然后一步一步逼问他,直到他崩溃为止。主播就是这样子,”程星瞳说,“直播需要你时刻保持高亢奋高紧张的状态,你只要干这行,你不可能不焦虑。”开播时,她得时刻关注流量曲线图,掉量了怎么办?要不要上福利款?“流量其实就是赛马机制,同时段开播的同类型的主播可能有10多个,就看谁的数据做得好。”她告诉凤凰网。
让她感觉恐怖的是,流量曲线图某种程度上和自己的活跃度是同步的。通常,程星瞳会在开播前喝杯咖啡,播到两个半小时,她一进入疲惫期,流量图就开始掉量,这个时候,她必须喝杯奶茶,被咖啡因一刺激,她回到亢奋状态,流量才能拉起来。
长此以往,程星瞳的睡眠成了问题: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除了流量焦虑,容貌焦虑也是悬在主播心头的剑。做带货主播之前,程星瞳做过几年游戏陪玩和语音主播,都不用露脸。后来她短暂做过一阵子唱歌主播,“小火了一下”,签约的MCN公司就让她露脸。“我当时脸长得肉,有婴儿肥,(五官)也比较平面,不适合上镜,可能现实中算小漂亮,但镜头里绝对谈不上好看,非常焦虑。”
她先是去割了双眼皮,后面又去做鼻子,自认被整容医院“坑”了11万。开始双眼皮做得挺自然,但她不满意,重做,二次修复后“天都塌了”,“跟鬼一样”。有半年时间她没有照过镜子。“可能是人痛苦到极致也就释怀了。”现在,她接受了自己不完美的样子。做了带货主播后,她避开和年轻美女卷,去了“中大淑”(中年大淑女风)赛道,卖50多岁阿姨穿的连衣裙,也是风生水起。不过,她还是认为,“整容整得特别值,如果当初不去整容,我其实拿不到带货主播的入场券”。
做主播两年,程星瞳状态最轻松的时候是去年年初,她第一次做兼职卖羊毛衫,只用播早班。做兼职给主播带来的成长有限,她也不需要考虑团队配合,没有心理压力,“就是纯挣钱”。早上4点起床,6点开播,10点她就下班了。回到家,看到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就觉得特别治愈,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都属于自己”,因为早睡,身体也健康了不少。但是兼职很不稳定,春天一到,羊绒消费进入淡季,没什么人买,播一两小时就得下播了。
迫不得已,她又开始找工作。为了拿下最后一份高薪但要求一口气播5小时的工作,她花了7000元报了私教课,健身一周后,体能终于达到了要求。
但撑到去年9月,程星瞳的身体彻底垮了:气血两虚,说话说一两个小时就喘不上气,播不到三小时就双腿发软,站不住了。过去,她看过中医,医生建议她,要么换工作,要么别播晚场了,“不然到了40岁这身体就没法儿要了”。从那以后,她开始惜命,酒、冰西瓜、冰淇淋,再也没碰过。但这次,只播下午场,她也撑不住了。她休息了两个月。
程星瞳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一年到头除了两三个月旺季,大多数时候一个月的收入是三五万,听着很多,但刨去她每月1.5万的生活成本,一个月撑死攒2万,一年下来就是24万。“这年头24万你是能买车还是能买房?我觉得这24万跟我的身体健康、我的快乐相比,真的没有可比性。”程星瞳觉得,她不是物欲特别高的人,赚钱无法让她持续兴奋,相反,她会陷入迷茫,“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圈里有名气的头部主播,一场直播,淘宝、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加起来能卖300万左右,但她们每天要播6到8小时。程星瞳的身心都无法接受。
成为大主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程星瞳评估了一下,这条路太难走了,这位接近S级的主播选择了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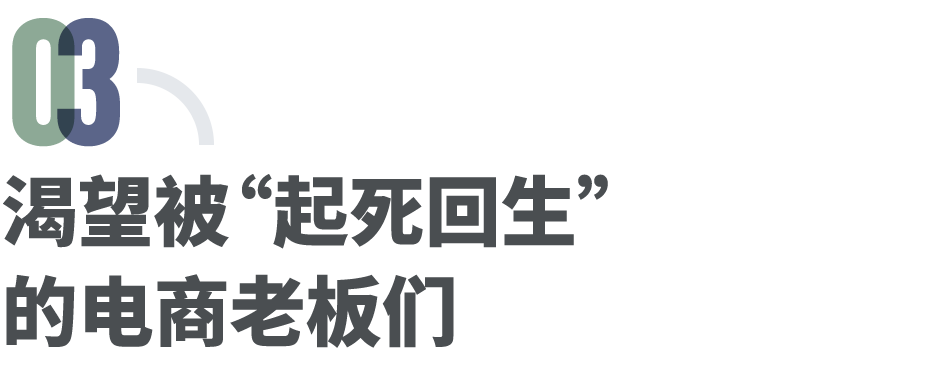
临走前,程星瞳换了赛道,做了一个月主播经纪人。她发现,老板们也不好做了。
拿她的最后一份工作举例。老板自己选品、备货,虽然每场能卖几十万销售额,“看起来好像挺唬人的,但是他的库存积压是巨大的,手里压了2000万的货”。这些年女装退货率高居不下,退回80%是常态,老板的钱都压到货上了。
团队已经把利润空间压到很薄,还是不断有同行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卷。今天出现一个女装爆款,立马就有对家把样衣买回去,换个便宜些的布料,等比例地抄。有些扛不住资金压力的老板,直接倒闭,大量清出尾货,这甚至也成了另一些人的商机。“我们之前有一个对家,专门收尾货,他的衣服按斤收,在直播间卖19.9,你怎么跟他卷?”更令老板们“难熬的”是电商税,今年双十一以后,单笔利润只有几毛钱的刷单商家、靠投流换取高流水的付费玩家,都要交税了。
老板不赚钱的情况下,也就没法像往年那样,给主播开出高薪了。
能开出高薪的老板,对主播的要求也更高了。“现在项目压力大,资金也紧张,老板们都很焦虑。大多数老板渴望的是,我可以给你高薪,但是你过来之后,你能带我们起死回生。”

程星瞳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的老板彻底放弃做货盘后,程星瞳出来看过别的工作。有个老板,欣赏她曾经的业绩,辗转了几个主播经纪人,买到她的联系方式。他们协定好,能卖到一定销售额就涨薪,卖不到,程星瞳就只拿能力范围内的钱。但是即便是在这个说好按劳分配的前提下,两天内播了两场流量平平的直播后,这位老板提醒程星瞳:“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直接带我们原地起飞的主播。”
在程星瞳看来,这显然不现实,熟悉团队至少要一个星期,把数据拉起来也需要时间。但老板没有这个耐心。
丽丽也遇到了类似的老板。2023年,丽丽从杭州一所本科院校毕业,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头部带货主播的公司,做商务助理。她在那里工作不到一年,因为接受不了加班到凌晨的常态,辞职了。今年年初,她再次回到杭州,发现房租降了不少。即便如此,丽晶国际的房租对她而言还是太贵了,她住到了滨江更偏远的地方。她频繁看工作,却感到就业市场的形势更严峻了。
从今年2月到6月,丽丽面试了30多家公司,找到了两份还算满意的工作。3月份入职的那家,她只工作了三周,因为业绩不达标,被辞退了。4月份入职的那家,重复了这个过程。
后面这份工作,是在一家护肤品白牌公司做品牌商务,她的工作内容是,联系达人主播,谈带货合作。为了让产品尽快上播,卖出销量,像丽丽这样的商务,老板一口气招了四五十个。公司实行末位淘汰,“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业绩谁就留下”。
尽管达人资源需要积累,寄送样品、待达人选品也需要时间,但“急于求成”的公司,等不了了。不到两个月,没完成35万销售指标的丽丽失业了。

除了货品过剩,更残酷的是,人大概也过剩了。
杭州政府的人才补贴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应届毕业生能得到1到1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和三年内每年1万的租房补贴。工作第一年,丽丽也拿到了综合1万元的补贴。她直言,当时留在杭州,“也是奔着补贴去的”。
不过,很快,丽丽感受到这个政策的另一面影响:“有些公司想着,既然你能拿到补贴,就会在工资上压低一点。”而且,再低的工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也是事实。
她后来面试的30家公司,几乎没有哪家能保证双休,单双休但不加班的也屈指可数。回过头看,丽丽才发现,只有加班问题的前公司“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双休,有年终奖,五险一金按最高比例缴纳。“走了之后才发现,外面这么难找工作。”可她已经回不去了。
失业以后,丽丽一边回想毕业那年,市面上月薪四五千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都不要她,现在竟然比那会儿还艰难,一边想到,即将有1222万比她更便宜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和她竞争同样岗位,不禁感到绝望。

◎ 滨江街头的房屋出租信息
不同岗位的人在不同面向上体验到了电商环境变差的事实。对丽丽来说,是今年6月她面试直播招商的工作,发现一个抖音粉丝几千万的账号,坑位费高达几十万:商家想让主播在直播间里带自家产品,就得付这个钱,哪怕最后产品没卖出去多少,也要照付不退。丽丽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和商家谈合作,“我一遇到这种招商我就头疼,感觉良心上过不去”。7月,丽丽决定离开杭州。试用期打折的底薪,覆盖不了她在杭州的生活成本。她把房子转租,搬到了浙江乡下。
在遥望科技的李雯,2024年就已经感受到行业不景气。标志是,那会儿公司开始做跨境直播,和北美主播合作卖货,去发展北美市场了。公司的直播成本越来越高,一场成交额1000万的直播,实际利润也就只有一两万百。今年年初,因为业务调整,李雯也被裁员了。
回老家后,程星瞳开始尝试她看中的下一个“风口”,短视频带货。“我入行的时候,主播基本都是打工仔了,实现财富自由的不多。但通过短视频带货买房买车的,我倒是见过很多,前两年真是满地捡钱,非常夸张。”她注意到这一现象是在去年7月,现在入场已经有些晚了,但程星瞳还是准备试试。钱不是终极目的,攒够钱后,她想去学心理学。

不过,尽管市场不再景气,但几乎所有对话者都认为,和其他行业相比,杭州的直播电商依然是有发展空间的行业。
程星瞳觉得,就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来讲,应届毕业生去做主播还是不错的选择,“我见过外形条件很好的,入行几个月就月入五万了”;在其他传统行业,这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年积累的时间。快速攒钱,锻炼销售能力,每天和公司的核心层打交道、学习,“之后你再去做其他事情,肯定事半功倍”。
李雯现在去了广州,给品牌方做店播策划。区别于李佳琦式、卖各品牌产品的达播,店播指品牌方自己开直播间,主播是工作人员,一天直播18小时是常态,有时直播间可能就十几个观众在。日成交额在10万左右,品牌方就觉得还不错。店播不像达播那样,要求每一场直播都精心准备、有漂亮的数据。“达人直播很重视场景,可能得花20万的成本去打造,但在广州,花20万成本根本不可能,你花个两万都要跟老板申请。”有时候,李雯也挺怀念在杭州时的直播氛围:促销机制搞得特别热闹,一个直播现场,十几号人因为成交额激动。
“你会觉得在杭州,你的天花板更高。”李雯说。
从7月到现在,丽丽在浙江乡下待了快半年。离开杭州的时候,她感到身边所有人眼里好像只有工作,没有生活。“辛辛苦苦上了十几年学,上完大学出来以后,发现努力也没有用,也没有机会。”她想要寻找一些不需要花钱就能拥有的快乐。
在那个小县城,丽丽租下两层小楼,一年租金3000元。她找了份工作,还是做品牌方商务,把县城老板的白牌产品送到直播间。工资五六千元,月休三天,没有五险一金。好处是工作压力不大,县城生活成本也低,没有了大城市的隐形消费后,她欲望减少,也不怎么花钱。
但她还是感到迷茫。“躺平一段时间可以,但我也知道不可能躺平一辈子。”当初,她执着于做品牌商务,也是因为这岗位有提成,能挣到钱,业绩做起来的话,工资会很高。她不甘心一辈子只拿死工资。只是现实让她屡屡受挫。
丽丽打算躺过马年春节再看看机会。但还要回到杭州和直播行业吗?她开始犹豫了。
应对方要求,文中李雯、刘惠、程星瞳、丽丽为化名
作者 王雯清 | 编辑 阳千鱼
排版 魏蔚
上一篇:全红婵,水花会消失,但快乐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