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成都这群老师聊了这些心里话
9月10日晚7点,八位来自成都市中小学校的教育人,走上了「三尺之外」城市教育谈的舞台。
这是红星教育传媒在第41个教师节前夕发起的一场教育谈话节目,也是我们对教育人的一场致敬——他们的所行需要被看见,他们的所思也需要被听见。
八位一线教育人,有人在沙漠中重塑教育的价值,也有人在AI时代守护人的意义,有人以数据拆解教育迷思,也有人以借远行寻找热爱的星火……他们拒绝用分数定义孩子,也拒绝让规模淹没个性。
字字句句,都是他们关于教育、关于成长、关于时代困惑的洞见。
本次活动在视频号“红星教育观”“学长来啦”“探校菌”及“海流-HAILIU”四大平台同步播出,创下了累计10余万观看量、3万余次点赞量的亮眼传播效果,让优质的教育思考获得了广泛关注。
这些讲述,不是经验的复述,而是思想的破茧;它们来自当下,却指向教育的未来。
在成为老师之前,陶思睿曾是一个被“优秀”绑架的人。作为一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却意外在高考失利。父母开始为此争吵,父亲甚至扇了自己两耳光,这让她意识到,“我的价值,必须用分数来兑换。爱,是有条件的。”

从此,陶思睿的人生进入了一场漫长的“自证”游戏。她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复读,像追逐救命稻草一样追逐分数,只为证明一件事——“我值得被爱”。
直到在大学遇到了恩师付老师,付老师带她去品尝美食、去赶海、做她的倾听者,告诉她,即使不优秀,也值得被看见。“付老师像一束光,照见了我这个‘人’本身,也照见了那个被分数遮住的我。”陶思睿也终于明白,“有条件的爱是枷锁,无条件的接纳才是钥匙。”
如今陶思睿成为教师,目睹太多孩子如她一般。“我们总是习惯于给学生打分,却忘了他们本来就不是一张待批改的试卷。我的使命,是做一个‘安全的容器’,告诉每个孩子,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再来。”在她眼中,教育不是打造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模板,而是守护一颗颗敢试错、敢不完美、敢为热爱而努力的真心。
邱祥迪戏称自己是“debuff”叠满的英语老师,“AI先是要干掉老师,又要干掉英语。”戏谑之外,真正让他思考的是:在这个专业快速消亡、行业剧变的时代,怎样让孩子终身保持竞争力?
仅2023、2024年两年时间,全国有超3000个专业被撤销,从英语、金融到计算机,没有哪个专业能承诺“一生无忧”。盲目追逐热门,反而可能陷入“填坑”的命运。
从教过的一千多个学生中,邱祥迪发现,真正站稳脚跟的人,都有三种核心能力:思考力、学习力和反思力。而这,正是新高考的改革方向——考查现实逻辑推演,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共情与换位思考的能力。
邱祥迪认为,保持终身的竞争力,不是“一时赢在起跑线”,而是“有持续进化的生命力”;不是“选对一条路”,而是“拥有走任何路的能力”。
新高考志愿组多达45个,为什么孩子还是找不到喜欢的专业?在殷黎看来,并非孩子没有热爱,而是在“有用”与“无用”的评判标准下,很多热爱早就被掐灭了。

在很多时候,奥数、竞赛、编程这些能加分、能升学、能为未来铺路的事,都拥有最高优先级。当“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成为默认规则,反而可能带来更负面的结果。从教35年,殷黎见过太多因此而封闭自己的孩子,而解局的关键,就藏在那些“无用”的事里。
“孩子就好比一个木桶,大家总在关心:孩子的‘长板’能不能更长?‘短板’能不能补上?所有人都一心想让这个‘木桶’的储水量更大。”但是要知道,木桶能装水的前提,是要有一块完好无损的“底板”。
而这块托举成长的底板,正是由那些“无用”的热爱、快乐和坚持构成。“我们都希望孩子成绩优异、‘长板’突出,但所有的期待都该有个前提:先跳出有用、无用的狭隘评判,帮孩子搭建一块厚实稳固的‘成长底板’。毕竟,只有‘底板’扎实了,那些关于分数、关于未来的长板,才有意义、有支撑。”殷黎说。
重点班的亮眼成绩,是“因”还是“果”?在许多人眼中,重点班被幻想成有“点石成金”魔力的地方——仿佛只要进入,就等于拿到了通往名校的保险。而张其从统计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误区。
重点班的形成,本质上是一次“选择性抽样”,学校通过筛选机制,将成绩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起,而非这个班级本身拥有魔力。张其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同样的花盆,不同的种子,最终植株的高矮取决于种子本身,而不是花盆。
面对家长们对顶尖名校的执着,张其给出了另一组数据:全国高考生中能上清北的仅占0.05%,上985的不到2%——概率低于中彩票。“家长自己买彩票没中奖,他不会觉得彩票有问题;但孩子没考上清北、985,他们觉得是孩子的问题。”
在张其看来,优秀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如果用体育成绩来分班,那么坐在重点班里的将会是另一批学生。“最好的教育,不是把自家的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支持孩子的成长,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找到属于他的那个人生的‘重点班’。”
一提到青春叛逆期,很多家长就如临大敌,甚至将孩子送进所谓的“矫正学校”,仿佛叛逆是一种必须被消灭的疾病。但实际上,“青春叛逆期,并不是一个必须要被消灭的‘问题’,它就像孩子会长高、变声,只是成长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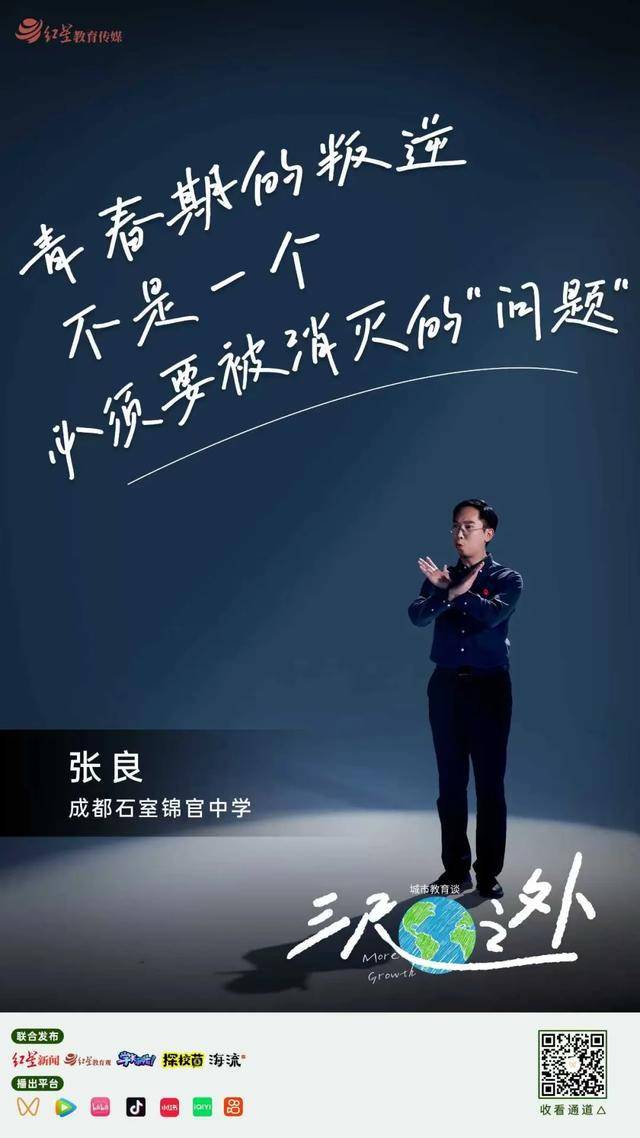
他举例说,在一个“叛逆”高中男孩的自述中,烫发只因崇拜球星,那是他第一次认真思考“我是谁”;而进入高中后,他主动剪掉了烫发。“探索往往是阶段性的,孩子会自我调整。”张良说,“是家长过度解读了孩子的行为,并且给这些行为贴上了‘变坏’的标签。”
同时还要注意,不叛逆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我们叫它“好孩子后遗症”。张良以吴谢宇案为例,告诉大家完美表象下可能是极端的压抑,一旦爆发更具破坏性。也并非所有叛逆都该被满足,家长应在理解与包容的同时,守住底线、把握分寸。
张良呼吁家长“与时俱进”,把握宽严界限,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试错,将叛逆期转化为成长的契机,而非对抗的战场。他最后借《哪吒2》的台词总结:“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你的路,还需你去闯。”
杜红梅是一名竞赛班班主任,在她看来,许多家长对竞赛班存在深深的误解——认为“通过竞赛上大学”是一条捷径,而进入竞赛班,就必须超前学习。不少培训机构借机推出“压缩饼干式”的教学,“短时间内,学生记住了知识、学会了做题,但是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学到这些学科的底层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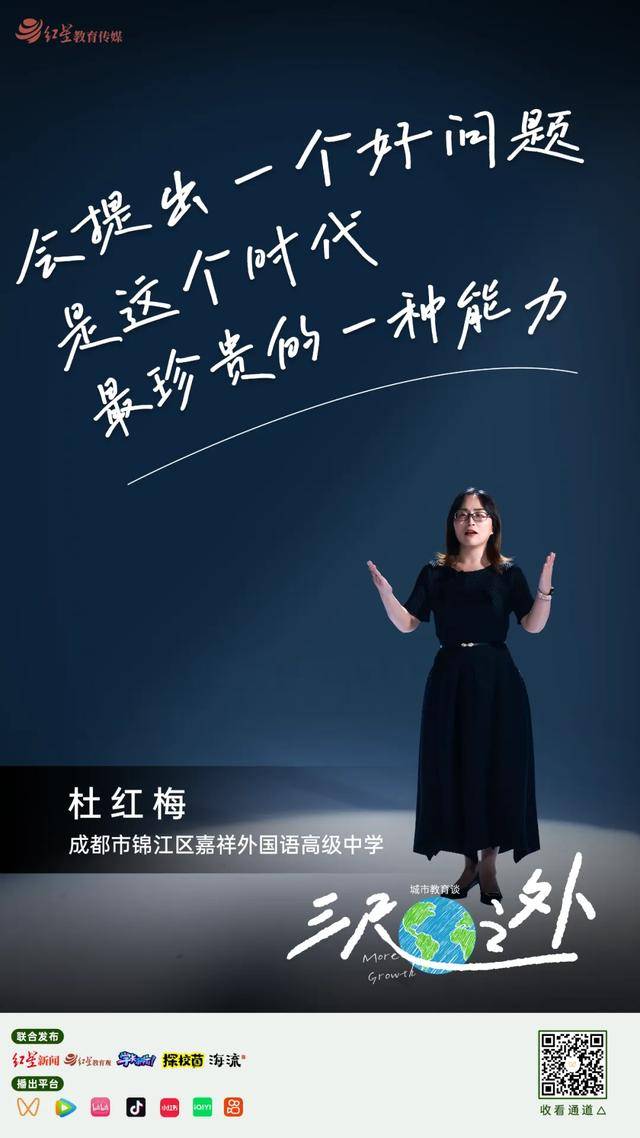
真正的竞赛教育,比的不是谁更擅长“给答案”,而是谁更擅长“提问题”。嘉祥竞赛班的选拔,有三条标准:一是对某个学科极致的热爱;二是高度自律的学习习惯;三是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拥有的不是回答的能力,而是提问的能力。”
“从选拔到培养,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提问生态’,鼓励学生从‘解题者’成长为‘定义问题的人’。”杜红梅通过带班经验发现,最终发展得最好、最有后劲的学生,未必反应最快、得分最高,但一定是最敢质疑、最会提问、最能持续思考的。
杜红梅说,当答案越来越唾手可得,“会思考问题,会提出一个好问题”,才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最珍贵的一种能力。教育最动人的时刻,不是训练学生重复标准答案,而是守护他们发出疑问的勇气:“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这个暑假,张克荣带着27个孩子进行了一次“教育逆运算”。在全世界都想让他们“无缝衔接”、疯狂抢跑的时候,他带着孩子们,向一片沙漠“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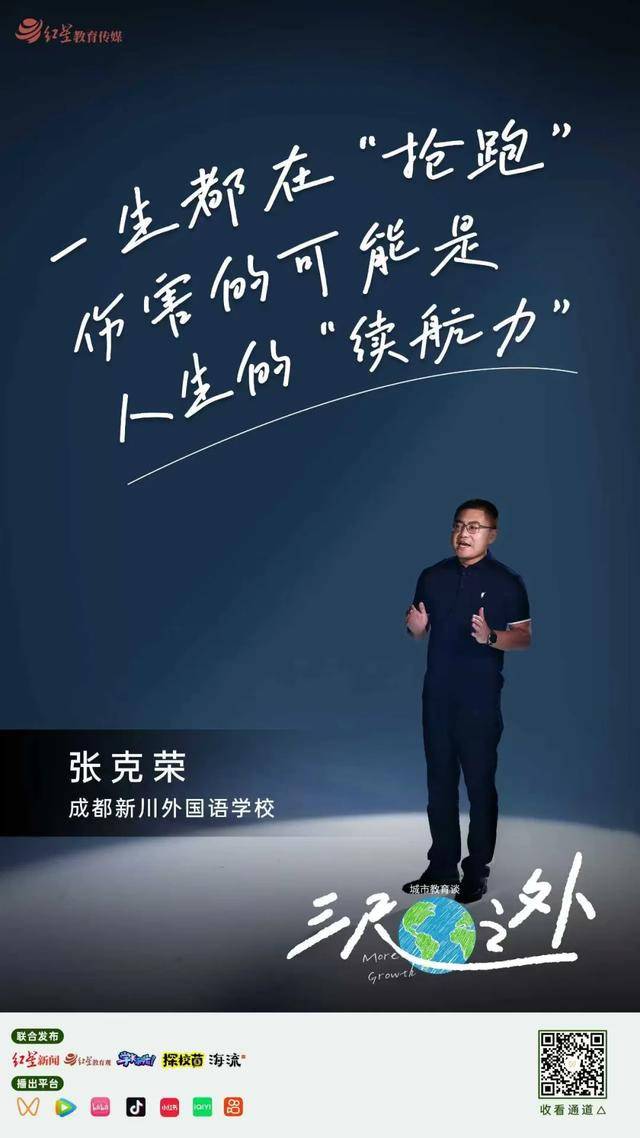
在张克荣看来,东亚孩子的一生,似乎都在被“赢在起跑线”这句话支配——胎教、早教、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考上大学还有高大衔接班、生涯发展夏令营。“他们试图把孩子的一生——从社交到恋爱——全部‘预制’完成。”而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工业化的流水线方式,精准地剥夺孩子最后一点“空白”,透支他们人生的“续航力”。
在甘肃民勤,没有题海与衔接班,只有真实的劳动与挑战。孩子们在沙漠中种下梭梭树,汗水滴落瞬间蒸发,却无人抱怨;在瓜田里,他们第一次真正体会“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群常被指责“沉迷网络”的Z世代,用直播的方式,帮助乡亲卖出六万多斤蜜瓜,解决了真实的难题。
张克荣说,这不是一次逃离,而是一场更高级的“刷题”——孩子们完成的是一道名为“生活和生命”的压轴大题。他们的价值不再由分数定义,而是由他们能守护的东西、能解决的问题重新彰显。他坚信,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世界搬进教室,而是把学生放进真实的世界里。
作为一位拥有18年教龄的教育工作者,钟巧始终关注这个反复被提及和讨论的命题:教育的规模化与个性化,是否只能二选一?她坦言,许多人将“规模化”视为流水线式教育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正是规模化,奠定了“人人有学上”的公平基石,让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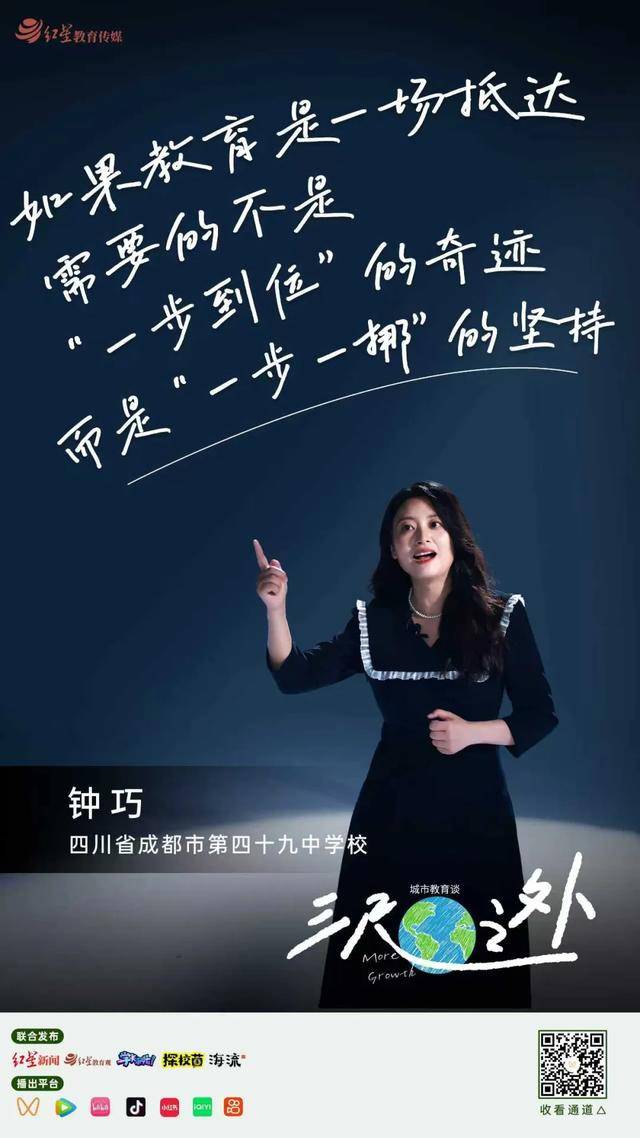
随着时代向前走,规模化的局限也在渐渐凸显。社会需要的不再是“通用型”人才,而是“创新型人才”;家长也不再只盼“有学上”,更希望孩子的特长被看见、个性被尊重、天赋不被埋没,于是,也就有了更多更个性化的诉求。
但“个性化教育”的落地,却是困难重重,现实最大的挑战在于师生比。一个老师面对50个学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顾全每个孩子。钟巧认为,规模与个性并非对立,而是教育的一体两面。学校曾尝试用“笨办法”实现个性化:备课三份、问题三层、作业三版——让每个孩子按自己的节奏进步。但这意味着每个老师的工作量几乎翻了三倍,并不长久。
后来受北京十一学校“选课走班”模式的启发,她带领团队重构了“三底课程体系”,以底线课程守根基、底色课程挖特长、底蕴课程育能力,并扩大分层走班试点。她清楚地知道,改革伴随未知,但她相信,教育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奇迹,而是“一步一挪”的坚持。“只要我们脚步不停,无限地去接近,就一定能让‘更多孩子被看见’和‘每个孩子被照亮’同时发生。”
三尺之外,
也愿这些声音如晨露滴入土壤,
让思考生根,
让改变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