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高达10万,7千名银龄教师走红!师范毕业生怎么办
2024年秋,陕西安康高新区的教室里,五六十位鬓角染霜的老者争抢“银龄讲学计划”岗位,60岁的退休教师胡玉明便是其中一员。
这并非个例:江苏单月放出200余个银龄教师岗位,徐州沛县仅城区小学就招聘144名;云南计划 2025年招募719名银龄教师,正高级教师年薪达10万元。
与此同时,“毕业即失业”成为部分师范毕业生的困境,在生源减少的背景下,银龄教师的“受宠”与青年学子的“遇冷”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教育领域的深层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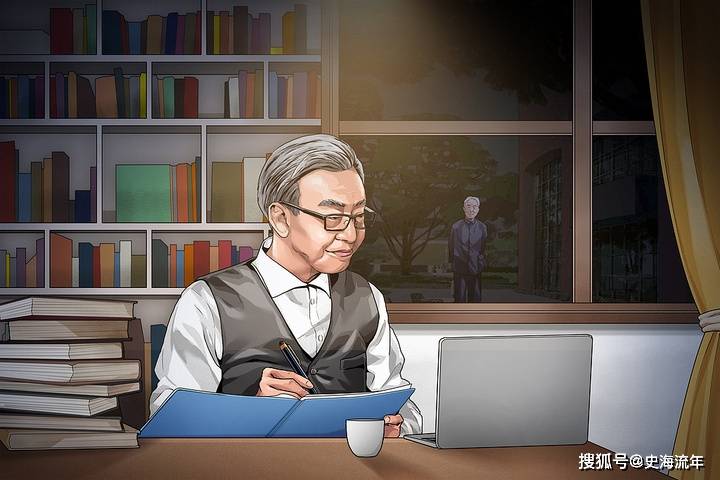
银龄教师走红的核心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与政策的精准引导。从供需结构看,我国师资呈现“总量过剩与局部紧缺并存”的特征:重庆忠县农村小学每千名学生配备144.6名教师,城区仅57.9名,城乡师资比相差近3倍,农村学校“无生可教”与城区学校“教师紧缺”形成反差。
学科结构矛盾更为突出,城口县乡村校音体美教师缺口达37%,景东县招募的银龄教师全部集中在高中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这类岗位恰恰是年轻教师不愿涉足或能力不足的领域。

政策层面,教育部2024年明确“银龄讲学计划”招募7000名教师,重点投向脱贫地区和乡村学校,中央与地方的经费补助更降低了学校用人成本。
此外,银龄教师的经验优势不可替代——罗源县要求银龄教师每周承担2课时青年教师指导任务,景东县则限定需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及县级骨干教师荣誉,这种“带教+授课”的双重价值,是应届毕业生难以企及的。

从师范毕业生视角看,银龄教师再就业带来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短期来看,竞争压力确实存在:徐州沛县城区小学140个银龄岗位若面向应届生招聘,本可缓解当地就业压力。
但从实际需求看,银龄教师的岗位多集中在乡村薄弱学校和紧缺学科,与师范毕业生青睐城区、主科的就业偏好形成错位,直接竞争有限。

更值得关注的是积极效应:其一,银龄教师填补乡村教育缺口,客观上延缓了部分地区教师编制缩减速度,为毕业生保留了潜在岗位。重庆忠县通过“带岗分流”盘活存量师资后,仍需银龄教师补充乡村紧缺学科,说明师资需求并未因生源减少而消失,只是需要更精准的人才匹配。
其二,银龄教师的“传帮带”机制为青年教师搭建了成长平台,罗源县要求银龄教师指导青年教师公开教学,这种 “经验传承” 能加速年轻教师的职业成熟。

其三,现象本身为师范教育敲响警钟,促使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加强音体美、乡村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长远来看有助于化解结构性失业。
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实现“人岗精准匹配”。银龄教师走红并非对青年教师的否定,而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

对师范毕业生而言,与其纠结于银龄教师带来的竞争,不如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既能像“走教教师”那样填补乡村学科缺口,也可借助银龄教师的经验提升能力。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进一步完善“银龄教师补充紧缺”与“青年教师扎根基层”的衔接机制,通过编制动态调整、待遇倾斜等措施,让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各展所长。
唯有如此,才能在生源结构变化的浪潮中,构建起老中青结合的优质教师队伍,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