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队》:平凡英雄淬炼人间烟火

一支失散的小队,一场“归队”之旅,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抗战故事。
电视剧《归队》拍的不仅是宏观上的抗战史诗,更是微观上的人性抉择:敌我悬殊,是战是降?至暗时刻,何以支撑?孤悬敌后,怎样取胜?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鲁长山俯身捡起路上的马粪,将马粪掰开,食用其中未被消化的玉米粒。《归队》以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开篇,将观众拉回到了80多年前东北抗联最艰苦的岁月。
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播剧目,《归队》的选材角度在某种意义上和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很像,它们都拍熟悉的战争题材和苦难的民族历史,都带有一定的“命题作文”色彩,也都试图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故事体验。
反映东北抗联历史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但多集中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电影《归心似箭》《最后八个》《步入辉煌》等。千禧年后,影视创作者鲜少涉猎这段抗战史,只有电视剧《闯关东》和电影《悬崖之上》有所提及。随着时间的湮没,这段抗战史也就成了抗日题材中的“冷门题材”。
而《归队》最大的特点,恰恰便是以史为据。它以日本盘踞东三省、持续施行“大讨伐”“归屯并户”“保甲连坐”政策为背景,在饥寒交迫的极端条件下,刻画了那段黑暗历史中东北人民所遭受的屠杀、迫害、奴役与精神摧残等一系列暴行,并深情还原了东北抗联战士们在白山黑水间的峥嵘岁月。

剧名“归队”指的不仅是“回到队伍”的物理动作,还是战士们重拾身份与认同的精神锚点——当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找不到方向时,“归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念想。
换言之,《归队》真正想讲的是:一群被时代倾轧的人,如何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里找到精神归属?
与以往抗战题材创作多聚焦于宏大战场和激烈战役不同,《归队》更倾向于从更细微、更日常的视角切入历史讲述。故事一上来就交代了主要的叙事脉络:
一支抗联队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被日军打散,排长鲁长山、二班长汤德远、神枪手田小贵、卫生员兰花儿、战士高云虎和万福庆六人活了下来,他们分走四条线路,有的遇上了进山的采参队,有的被骗进老金沟做起了淘金工,有的被抓进日本劳工营生死一线,有的潜入土匪窝和土匪打成一片。
突围、失散、寻找、变故、归队,从打散到重聚串联起了《归队》的故事主线,进而从个体经历出发,通过多线叙事,描述了不同的人物群像。
这种多线平行、交叉推进的讲述方式,将不同空间、不同境遇的人物串联了起来,拓展了剧集的空间维度。从东北大森林到淘金沟、劳工营、土匪山寨、松林镇,皆展现了日军侵略下不同的社会侧面。而参帮的民俗规矩、淘金工的悲惨遭遇、劳工营的人间地狱、山寨里的“江湖道义”等具体的情节设置,则让该剧呈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风貌与地域质感。
鲁长山与田小贵意外闯入参帮,目睹了参帮为争夺一株百年老参付出17条性命的代价,并最终意外获得了这株老参。为了实现参把头卖参为部队筹集物资的遗愿,二人周旋于阴险特务与精明商贾之间,展现出了非凡的生存智慧。

万福庆先是与高云虎落入老金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矿难,逃出生天后又与汤德远一同陷入暗无天日的日本劳工营,在非人折磨中坚守抗争火种。而汤德远在被日伪堂兄救离劳工营后,则饱受思想挣扎,一度在“归队”问题上产生动摇。
兰花儿负伤后,被落草为寇的葱山小白马所救,两人渐生情愫。然而兰花儿始终不忘归队的使命,试图以抗日大义说服小白马,带领匪帮下山抗战。
与此同时,高云虎在矿难中侥幸生还,被豪爽泼辣的酒馆老板娘大阔枝收留。他暗中查出老金沟管事故意制造塌方事故、以残害矿工性命骗取抚恤金的真相,决定杀死幕后黑手游世龙,为死难工友讨回公道。
这些线索既独立成篇,又彼此交织,共同绘就一幅战争侵袭下的东北浮世绘。
通过每个人物的独特经历,创作者有意识的为“归队”主题扩容,赋予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对鲁长山来说,归队是组织与责任的召唤;对汤德远来说,归队是忠孝两难间的权衡、抉择;对田小贵来说,归队是褪去少爷身份、在战火中重塑自我的淬炼;对兰花儿来说,归队是革命理想与个人情感相交融的毅然奔赴;对高云虎来说,归队是告别温柔乡重归战场的艰难转变;对万福庆来说,归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
无论大家经历了何种境遇,他们一直铭记着离散前的约定: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而战士们将怎样归、何时归,也构成了剧中最引人入胜的麦格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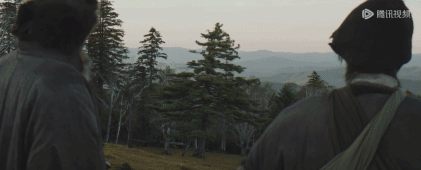
另外,多线叙事也让该剧呈现出了一种“公路片”的类型感,充满了“奇遇”“博弈”等元素。以“挖参”线为例,乱世之下百姓生存艰难,两拨参帮为一株人参大打出手,又有土匪隐藏身份潜入做局,一锅乱斗的情势下,鲁长山和田小贵既要隐藏抗联身份,又要想方设法地走出密林,这种背靠抗战背景对类型元素的深加工,让《归队》的故事具备了更多元的可看性。
在各条叙事支线中,大家几乎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困难,有的为己,有的为人,且面对各个初次相识的支线人物时,敢信敢帮,敢爱敢恨,敢打敢拼,快意恩仇……这种具有侠气的人物形象塑造,让人物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具有了一定的传奇色彩。
如此,归队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诉求,一种执念。这让《归队》突破了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框架,升华为一部关于信念、成长与生命选择的时代寓言。

冷峻风格与烟火气息交相辉映,为《归队》搭建出了东北在日据时期的叙事场域,也让故事营造出了一种扎实的东北美学。
据悉,剧组曾深入辽宁、吉林等地的林海雪原,在艰苦环境中进行实景拍摄。这让它在艺术表现上立住了阵脚。镜头下的东北既有白山黑水的广袤厚重,又有荒原雪林的肃杀粗犷。尤其是“八棵松”的象征意义,更是呼之欲出——在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中,一棵又高又直的松树屹然挺立,蔚为壮观,是抗联战士们精神信仰的视觉化身。
不仅如此,创作者还在剧中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从掰马粪、嚼婆婆丁到硬到硌牙的菜饼子、露出飞絮的大棉袄,无不成为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注脚。
具体到角色身上,“吃”这个意象占据了大量篇幅,成为剧中人物重要的情感联结:土匪小白马向兰花儿示好,靠的是在吃上下功夫,笨拙的用荤菜示爱;大阔枝与高云虎结缘,同样少不了吃食上的助力,不仅用肉蛋饺子拴住了对方的心,还让“家”的意象得以具象化;鲁长山跋涉回家后,妻子铁梁娘拿出来迎接丈夫的“宝贝”,亦是一顿久违了的白面条。

通过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吃食,《归队》完成了从“活下去”到“怎么活”的精神升华——尽管归队不易、战斗残酷,但战士们为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为了守护他们的家人,守护千千万万个小家,以及屋檐下的普通老百姓。
相较其他抗战题材作品,《归队》对人性中的坚强与软弱进行了不错的平衡处理。它将叙事根植于真实的历史肌理与人性逻辑,没有将英雄的坚定表现为从不动摇,而是着重刻画他们于小家与大家、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之间所经历的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
汤德远逃出日本劳工营回乡后,面对年迈体弱、亟待照顾的父母,一度陷入“尽孝还是归队”的挣扎;鲁长山回家后,面对守候多年的妻子和不肯认爹的儿子,心里充满愧疚;田小贵衣衫褴褛地回家后,让地主父亲又气又心疼,而田小贵也差点被热炕头磨了心志;高云虎在大阔枝的酒馆里体会到了“家”的温暖,也削弱了他重返战场的决心……
这些细腻真切的情感刻画,不仅没有削弱英雄形象,反而让他们更加血肉丰满。因为他们不仅是战士,也是儿子、父亲、爱人,有着普通人的牵挂与软肋。在犹疑、痛苦与自我拷问之中,他们的选择显得真实且珍贵。
这种回归人性的温度,让剧集在传奇与“奇观”之上,保有了对历史与现实最基本的尊重与敬意。它无意塑造完美英雄,也不呐喊宏大的口号。而在大时代中寻找到一个个在绝境中奋勇挣扎,在迷茫中坚定信仰的小人物,以他们为原点,触碰流动的人性,激发出最广泛、最永恒的共情。
这是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家国同构。剧集从“小人物见大历史”的创作理念出发,由小及大地将“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劣”的宏大抽象的国家历史化为微观而具体的个人记忆。
经由六名“归队”战士的视角,它见证了抗联、参帮、土匪、伪军、普通百姓等人在战争侵袭下的悲惨遭遇,进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让观众从个人悲剧中切身感受家国之痛,进而完成民族记忆的建构。
冻土之上,归途滚烫。这份真诚与鲜活,在当下仍具有熨帖人心的温度与力量——它关乎信念,关乎选择,关乎每个人在时代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No.6540 原创首发文章
|作者Nico
简介:资深娱评人,深耕文娱领域,凤凰电影、visa看天下特约撰稿人。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欢迎点看【秦朔朋友圈】
上一篇:《灼灼韶华》:韶华和闺蜜坦白伤痛,艰难之时永远会彼此照耀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