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老人如何养?

老龄化昭示着新的商业需求与时代机遇。未来的退休金足够养老吗?养老的钱还能从哪里来?社会上哪些养老方式和服务是可靠的?如何有尊严、体面地老去?——这都是需要直面的民生问题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国庆中秋假期,“短托养老”进入更多人视野。在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的三家养老服务机构,假期需要出行的儿女,每天花费99元,便可以让老人住进养老中心,获得一日三餐和日常照料等服务。尽管社会化养老服务愈发便利,但尖锐的担忧也被抛了出来。
今年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协会内部会议上,高传捷几乎是拍案而起:“老年人等不及了。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些老年人在养老院里、在家里头忍受欺负,怎么办?”
这位原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年轻时从事金融监管工作,步入老年后,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社区慈善信托、家庭财产传承等领域。前阵子,他在北京大学遇到一位80岁的退休教授,太太去世,孩子们“躲”在国外,不愿回来,只得请保姆来家中照料。
“保姆在家里拿着手机玩,这是不作为,我们还没看到那些打老人的,对不对?”高传捷将这些儿女在国外、养老无人依傍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失独老人”。他发现,即便退休金较高的人群,年老失能失智后也会面临类似难题。养儿防老,慢慢瓦解,这是我们时代的新课题。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空巢老人规模近1.5亿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达772万人。另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中国老年人中独居的占14.2%。眼下,当代中国家庭,一对独生子女夫妻(两人)可能需要赡养四位父母,抚养一两位孩子。职场竞争激烈,中年失业压力盘旋,子女往往自顾不暇。
随着中国总和生育率走低、单身人口增多,老无所养、老无所依,不会只是社会的个例。民政部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达3.1亿人;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突破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不过,数据具有些许迷惑性。截至2024年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社会对年老的认知正在重塑中。一些观点认为,生活医疗条件改善后,60岁不足以成为衡量是否衰老的门槛,“40岁是青年,60岁是中年,80岁才到老年”。
从时间维度拆分“养老”,大致可以分为备老、享老、终老三个阶段。昆仑信托总经理江昱洁向《财经》介绍,四五十岁起,我们就可以从资金等方面为老年生活做准备筹划。退休后,开始享受老年时光,又可以细分为颐养、康养、医养三个小阶段。最后是终老。
时不时,“银发经济”被寄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厚望。交通银行养老金融部总经理李利测算,随着60后和70后步入退休年龄,这部分人群持有的储蓄、理财、基金、保险四大类金融资产加起来120万亿元,其中储蓄存款接近72万亿元,占据社会财富51%。未来十年将进入“银龄财富时代”。到2030年以后,全社会60%甚至70%的财产将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老龄化昭示着新的商业需求与时代机遇。然而,对每一位个体而言,我们的关注重心仍将回归自己的处境:未来的退休金足够养老吗?养老的钱还能从哪里来?谁来养老?哪些养老方式和社会服务是可靠的?如何有尊严、体面地老去?——这都不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忽略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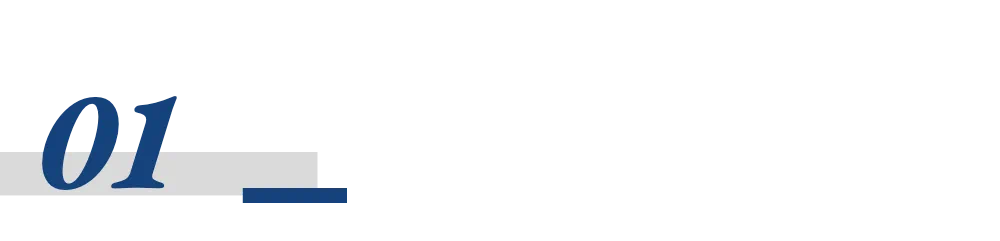
结伴养老,胜过与子女“一碗汤”的距离
樊沈英和她的丈夫刘凤江是那种“翻墙”也要入住养老院的40后老年人。
1994年,从事外贸业务的刘凤江被派驻美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工作,樊沈英随同前往。那期间,他们到美国的养老院拜访同学的父母,吃惊地见识到,养老院的生活居然可以如此体面、舒适。美国的养老社区成熟,有的已经建成百年,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千禧年回国,两人接近退休年纪。一次去北京小汤山的路上,他们偶遇太阳城养老社区项目正在开盘。那是2002年,两人将车停在路边,驻足参观,没想到太阳城和美国养老社区的理念如出一辙,承诺配套各类体育、医疗、文化设施。当天,他们签约交了定金。
从2003年入住算起,他们在太阳城社区度过了13年的快乐时光,结识了许多真挚的朋友。后来,开发商和项目日渐衰败,养老社区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他们在2017年退出太阳城社区,到顺义区的龙湖小区置办了一套房产,和女儿的家只隔着“一碗汤”的距离。
“女儿也承诺给我们养老,我俩本意并不想用这种方式。”在龙湖小区的家,樊沈英和老伴亲力亲为,做适老化装修改造,轮椅在家中来回转动也要宽宽绰绰的。直到2018年,他们在小区附近溜达,注意到一处蓝色铁板围着的地块,尚未开发,竖着一块白色牌子。上面写着“北京A61养老用地”。
两人扒着板子往里望,四周荒芜,只有几个楼座子,全是野草。他们去观望了11次,“翻墙”进去考察。2020年7月初,红色的新楼挂出“和园长者社区”的牌子。樊沈英上网查,这是首创城发与远洋集团共同推出的养老项目,由旗下叫做“椿萱茂”的子品牌运营,料想这是上市公司的项目,应该可靠。
第二天,他们驱车到售楼处。大开间配两个卫生间、丰富的老年活动、综合的配套服务,立刻签了约。彼时只有宣传册,但樊沈英的老伴很坚决,至少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的做饭问题。他不在意家的形式,老伴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樊沈英还把两位亲家、两个闺蜜拉到了和园。
迄今,和园开业运行四年,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总共372套房,目前入住了155位老人。放在全国看,它都属于那种高端养老社区——7栋小洋房围合,形成了一个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200米的宽敞内庭院。咖啡会客厅、瑜伽室、书法室、电影间、图书馆、健康护理中心,一应俱全。每天早上,社区组织老人们做保健操和增肌操,这两套操分别和301医院、协和医院联合研发。不定时,社区还会组织日韩邮轮游、去成都、去庐山。

左图:北京顺义,椿萱茂·和园养老社区,入住老人的画作。右图:椿萱茂·和园养老社区的图书馆,摆放着入住老人捐赠的竖版鲁迅全集。摄影/邹碧颖
《财经》记者到的那天,一些老人刚坐上大巴,外出观看陈佩斯的电影《戏台》。入住和园的老人,大多65岁以上,九成以上是“活力老人”,能够独立自主生活。每位老人配有管家,每周享受两次入户的深度保洁。夏天,床单每周会更换一次。这里车程半小时内,有顺义区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北京怀柔医院,一些专家定期会来和园坐诊。
像这样的高端养老项目,收费不算便宜。小一点的开间,月租在8000元-1万元左右,入住一人加6000元左右的服务费,水电气网、餐费、各类医疗活动服务费用包含在其中。大些的房间,月租1.4万元左右,服务费略贵几百元。
入住和园的老人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用退休金或儿女收入负担这笔开支;也有像樊沈英,将自家房子出租或出售来供给养老院。“钱要为我所用,如果不花到我们身上,一点意义都没有。”樊沈英想得透彻,“70年也罢,50年也罢。我们未来养老能够妥妥帖帖地安排,没有后顾之忧。至于我们咯噔闭眼了,这个东西还有没有价值,于我来讲有什么意义?”
樊沈英的老伴曾在龙湖的家中发过一次病,两根棍子兜着软布做成担架,楼上楼下找保安帮忙,抬进了电梯。2024年,老伴在和园病倒,工作人员从旁协助,救护车经由专门的通道来来回回31次。樊沈英想,幸亏来了,“这一年跑医院,我几点进门、几点有饭吃”。
老人们和儿女的关系亲近而有边界。过年是和园最忙的时节,家宴从大年三十开到正月初五,每天10桌以上。子女亲属请长辈回家过年,有的老人会说:“这是我的家,凭啥让我去你家过年?你得来我家。”公共咖啡厅一到下午总是热热闹闹,还有老人在弹钢琴。
准确来说,这是一套精品化老年生活方式。受美国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模式启发,和园有一套CLRC(持续生活退休社区)养老理念。“不是说你在家里找一个保姆,而是吸引他从家里出来,享受各种各样的活动、健康管理。”工作人员邱钰程对《财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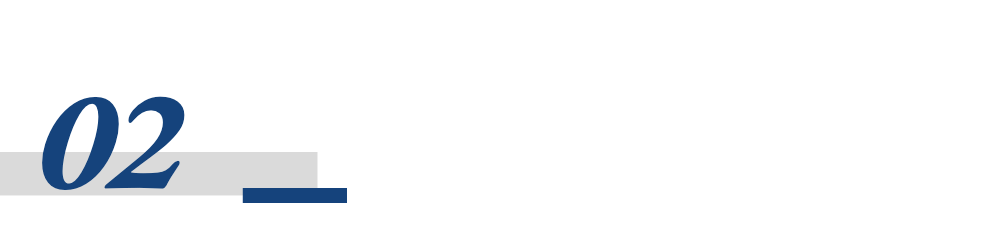
优质养老院兴起,家庭财力可否支撑?
那种潇洒的老年生活,车耳在美国工作时很熟悉。他曾担任中信集团驻巴黎代表、驻纽约总代表。20世纪90年代,车耳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里工作,住在曼哈顿下城。旁边是风光旖旎的哈德逊河和各家投行所在地。有一天,河边突然开始盖一栋红楼养老院。
“不像我们的都建在郊区,他们把养老院建在金融机构旁边。”每天,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步履匆匆,周边学校的阳光少年进进出出。车耳通勤的路上总会路过那家养老院。平日,老人们穿戴整齐,按点到楼下吃饭,还有各种打牌旅游活动,圣诞节和孩子们聚一聚。
每隔一段时间,车耳能看到救护车从这栋红楼将人拉走。一次开放参观机会,养老院的经理领着车耳在里面逛了一圈。他明白了,“很多人进到这栋楼,就是人生最后的归宿”。
但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家庭财力不足以负担这类优渥而舒适的养老社区。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相关负责人曾介绍,中国形成“9073”的养老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传统观念对养老院的认知停留在过去。邱钰程发现,舆论担心养老机构虐老,儿女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往往被认为不孝,难免遭人非议,入住养老院亦需要老人越过心理关卡。《财经》了解到,养老机构会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设立接收门槛,传染病、精神类疾病通常无法入住。此外,入住养老院还需要监护人——法定监护人通常是配偶或子女——签字。
金钱是现实的另一面。入住养老院的费用,因城市等级、机构类型、老人自理程度的差异而不同。假设一位全护理老人住在二线城市的中端民办养老院,月费用约8000元,年花费约9.6万元。一个家庭有50万元存款,仅能支撑约5年,还未考虑通胀及费用上涨。
中国的养老机构层次多样,很难一概而论。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中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40.6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99.3万张。其中,国企、民企皆有布局。
政府修建的养老院主要是兜底保障型,例如福利院,针对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等弱势群体,收费较低。一些国有企业参与的公建民营项目,属于普惠支持型养老院,收费相对可承受、质量有保证。如果追求品质化的养老生活,往往需要寻求市场化项目。
目前,养老机构的中高端市场由地产商、保险公司主导。地产商是最早进入养老领域的社会资本,万科、保利、远洋地产推出了养老社区的子品牌,绿城、华润、招商蛇口同样有养老业务布局。中国人寿、泰康保险、平安集团也在探索保险与养老机构服务的联动。
险资主导的养老机构,《财经》记者拜访了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运营的“玉兰人家”项目。“玉兰人家”社区位于北京顺义,总建筑面积17.7万平方米,规划房间1387间,可以容纳超2200人。已经建成的一期项目,其中规划设有一栋社区医院。玉兰人家与顺义区医院合作,将设立玉兰园区。建设者希望,将来运营后可以满足老年人慢病管理、基础检查等日常医疗需求。

左图:北京顺义,玉兰人家社区的大开间,卧室图。右图:玉兰人家的适老化装修卫生间,足够宽敞,可供轮椅进出,并配有助力扶手。摄影/邹碧颖
《财经》记者看到,室外有一块门球场。工作人员说,天气好时,老人也用来打八段锦。节能建筑的墙体里埋设了u型“毛细水管”,冬天热水循环、夏天冷水循环,房间恒温恒湿。一期2024年10月开业,包括两栋公寓楼,目前开放561个房间,入住接近300人。每栋楼一层配备有小型医务室,医师、康复师可以检测血压、血糖。社区还有自己的餐厅。
这类养老院同椿萱茂的和园类似,是社区公寓+综合服务的叠加形态。《财经》了解到,“玉兰人家”一期的户型从52平方米到105平方米不等,最大的105平方米房间,是一室一厅。飘窗纵深1.4米,子女能躺下休息。卫生间铺着防滑地砖,马桶旁配了助力扶手。智能镜子可以显示天气预报、看视频听音乐、查询社区活动的课程表,乒乓球、广场舞、电影……
中高端养老院注定是少数人能负担的选项。高收入家庭拥有多套房产、金融投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只有一套住房和有限存款,现金流紧张。农村家庭,或许更难以企及。
家庭资产负债表揭示出居民养老家底。根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163万元。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分别为461万元、263.5万元、207.6万元、165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而且,家庭资产多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
这些年,“以房养老”的思路被屡次提及——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仍然继续生活在屋子里。保险公司每月支付一笔固定费用给老人,直到老人去世,获得房产所有权。2014年,原中国保监会开始启动“以房养老”试点。但据了解,十年过去,幸福人寿保险公司仅做了近200单“以房养老”业务。尽管“以房养老”能带来实在的养老现金流、许多家庭亦愿意抵押房产,但这些保险公司实际面临着资金长期“只出不进”的营收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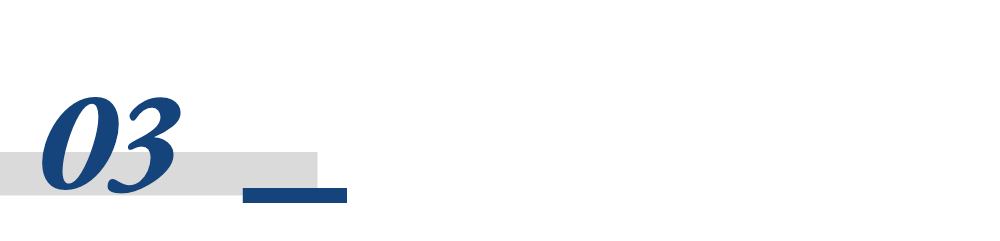
养老金降至工资的三四成,怎么办?
退休后,养老金能否成为晚年生活的保障?
中国的养老金被设计为“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政府强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主要是国央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建立,民营企业的参与度不高。第三支柱是2022年开始推开的个人养老金,主要依靠个人自愿储蓄或投资。个人每年可缴纳不超过1.2万元,享受递延纳税优惠。
东北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三支柱养老金规模合计近14万亿元,第一、二、三支柱规模分别达7.82万亿元、5.75万亿元、300亿元。另据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亿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各覆盖70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仍低。
养老金往往是第一支柱。年轻人缴费、供养老年人,实行现收现付制度,一些人担心可能收不抵支、在2045年耗竭。懿定坚扈公司创始人张偲,深耕养老行业多年,他告诉《财经》,1992年中国刚设立第一支柱时,只有缴纳、没有领取,随着时间推移,领取养老金的人变多,资金自然会愈发紧张。据财政部数据,2018年-2021年,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安排养老保险补助支出7.77万亿元,有力支持各地区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同时,张偲澄清,基本养老保险资金很难说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用尽”概念。毕竟每年有财政税收作为支撑。只是倘若财政填补的比例变大,必定会影响教育、医疗、国防等领域的开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之外,还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战略储备。2000年,全国社保基金设立,从2001年投资运营800亿元起步,至2023年末累积到3万多亿元。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冰山下的部分,必要时可调剂用于基本养老保险。关键问题在于,将来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券商研究显示,目前,中国7%人群的退休金每月7000元左右,以体制内为主。38%的企业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大概3000元,55%的城乡居民月平均退休金是200多元。可见,第一支柱养老金,仅够保障基本生活,或难维持高质量的养老水平。
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树清发出警告,未来中国第一支柱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之比)可能降至30%-40%,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最低替代率55%——第一支柱当期支付压力过重,第三支柱能否缓解中国的养老金压力?
通俗而言,第三支柱是政府信用背书,严选出一批商业理财、保险产品,供公民自愿挑选购买。在发达国家,第三支柱往往是养老金的重要补充。例如,美国的第三支柱占其积累制养老金总规模的约三成;日本长期以第一支柱为主要来源,改革后,第三支柱也占到10%。但中国公众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度不高,第三支柱资金积累量和参保人数迄今不及预期。
张偲分析,第三支柱最初起源于加拿大,加拿大近四成联邦税收来自个人所得税,覆盖80%的纳税人群,个税优惠有力地激发了民众认购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而中国14亿人中缴纳个税人群占比不高,因此同样采取个税优惠激励,覆盖人群偏少,或难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管培曾在中意人寿、美国大都会、阳光保险等保险公司负责保险精算业务,是人寿保险领域的资深专家,她告诉《财经》,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在国内保险行业的保费占比不到10%。“80后”“90后”普遍缺乏养老储备的意识,实际上可供储蓄、做投资的钱也许并不多。就业环境不稳定,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大多需要每年坚持缴费,这会影响人们的认购意愿。
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20年至2024年期间,北京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3613元/月上涨至6821元/月,涨幅为88.8%;上海则从4927元/月涨至7384元/月,涨幅为49.9%。最低工资上涨缓慢,很多人拿着低工资、交着高社保,一定程度也挤压了商业保险购买意愿。
但管培提醒,年轻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能够起到强制储蓄的作用。大部分人30岁要养孩子、供房贷,40岁是购入商业养老保险的最佳时间点,60岁左右开始领养老金。保险,尤其是长期寿险或者养老年金保险,从长期利益的稳健性来看,相较其他中短期产品而言是更稳妥的。个人资金周转紧张时,也可以使用保单贷款向保险公司借款。
“如果未来保险法存在打破刚兑的可能性,选择长期经营的公司,可能才是更好的。”管培补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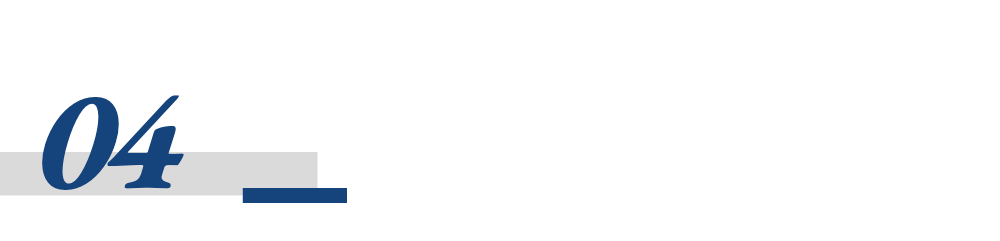
护工、长护险和社区支持,尚未就绪
钱,并非晚年养老面临的唯一挑战。管培开发过护理险、失能收入险,她发现,另一个问题是“买不到服务”,护理行业普遍请人难。《2024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养老护理员供给缺口达550万人,新增养老护理员的流失率为40%至50%。
陈清是北京康养集团的员工,为西城区白纸坊街道提供养老服务。他认识一位80岁的叔叔。叔叔曾请过护理员,有时反倒是做饭给护理员吃。陈清还发现,家属请人往往要筛选护理员年龄、工资等条件,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可供选择。护理员也有自己的入户偏好。
人社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原副主任白璐告诉《财经》,长期以来,城市养老护理员主要由农村富余劳动力充当。譬如在北京,今日东方公司和山西吕梁市合作,将当地农村劳动力输送至房山区。吕梁市出补贴,给每人配一个旅行箱、一件红马甲。经过一个月培训,这些阿姨在房山上岗。但工作几年,等到钱攒够了或者孩子要上中学了,她们就要回家了。
“不聊天,护工就是干活。”白璐还发现,市面上的护理员培训大多不含理论知识,很少讲授如何与老年人沟通、提供精神慰藉。职业院校有养老护理专科教育,这两年,国内也慢慢开设本科专业。毕业生虽然抢手,但很难在养老院坚持下去,工作两三年就离开了。
“传统观念认为,伺候人的事是低人一等的。”白璐说。同时他深知,专业的护理不只是简单的翻身、洗脚。社会观念需要转变,护理员的薪资待遇也有待提高。在北京、上海、深圳,护理员到手月薪多在6000元-8000元,不如其他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因此较小。
实际上,普通家庭很难为照护服务支付高额费用。人社部从2016年起在上海、广州、成都、青岛等城市开展长期护理险试点,一定程度上补贴失能老人家庭请护工的费用。然而,补贴资金主要依赖医保基金划转,一些试点城市基金结余不足,长护险现在覆盖面很小。
社会化照护服务的供给,至关重要。管培的父亲曾因小手术住院,她特意请假三天到医院陪护,每天盯着点滴瓶,一宿、半夜地熬,发现“这活太难干了”。中国人寿集团原董事长白涛曾谈到,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大概在4500万人左右,需要专业护理人员1000万人以上——等到父母80岁后,许多忙碌的独生子女,将不可避免求助于外部照护力量。
大城市里,一个个原子化的小家庭,面对深度老龄化时代的严峻照护挑战,寥寥无几的指望对象,是社区。北京康养集团是北京政府2022年成立的大型国企,其使命之一是探索普惠养老、社区养老。副总经理张硕告诉《财经》,该公司曾在北京做了一项覆盖10万多人的老年人调研,结论是99%的老年人将会选择居家养老——社区支持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白纸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北京康养集团将建筑划分为临街的社区食堂/老年学堂、三进院落的住宅和养老床位,以及配套综合服务等空间。平日,周围的老人能以2.5元/两的价格到食堂打饭盛菜。如有专业护理需求,也可申请入住后面院落里的双人间床位。国企运营,价格比同等条件的养老院划算。养老服务中心离家近,家人过来照看也相对方便。

左图:在玉兰人家,入住老年人正在照管自己的小菜园。右图:白纸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后院的公共活动区域。摄影/邹碧颖
街边一间小门店,电话铃声不断。陈清介绍,北京康养集团上线了“北康养e家平台”,家属可以预约158项上门服务,包括陪同就医、助浴、修脚、理发等服务,满足老人的日常需求。不熟悉手机的老年人也可联系门店工作人员预约。这其中,“京慧养”服务不同于家庭保姆一人的单薄力量,是五人管家医疗团队,可上门对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居家照护服务。
白璐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一定是未来养老主流,社区应当承担起更大的公共责任。他调研过宁波的大闸未来社区,那里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04人,占全部居民的23%,老龄化现象突出。但社区治理完善,驿站里有药事服务、智慧云药房,专业护理人员会定期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社区服务,还包括陪伴老人聊天、散步、打牌、下棋、绘画、编织等等。
基层养老服务,刻不容缓,农村同是如此。白璐结交的一位茶友,家住福建宁德市霍童镇。附近的卫生室,负责村民的基本医疗。大夫两人,日常坐诊之外,经常到老人家里串门,关心身体状况。茶友的爷爷病逝前,村里的大夫三天两头跑一趟,打吊针、输营养液。
社区自治、邻里帮扶,能否解决居家养老难题?《“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也提出,到2025年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乡镇(街道)的覆盖率总体达到60%。然而,目前全国许多社区人手不足,基层治理松散,日常活动少、邻里联系薄弱,尚难担起养老重任。
像北京,白纸坊服务中心今年7月一一给200多位街道重点帮扶老人打电话。陈清试图推介免费养老服务——每个月上门免费理发或修脚一次,再免费上门探访一次。“我们都觉得免费的不挺好吗?”然而,老年人的防诈骗意识极强,最终只有4位愿意接受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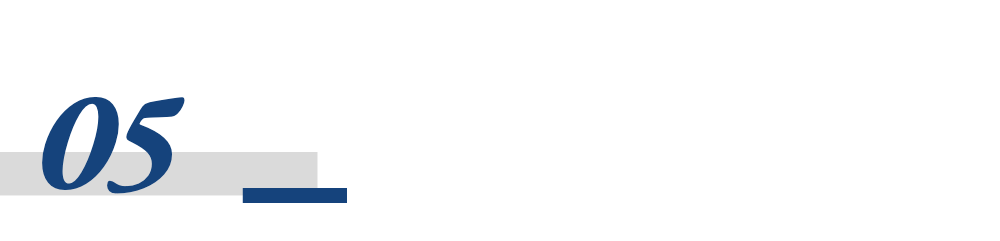
养老托付他人?银发时代的社会转型
“当前不少机构借‘养老’之名实施诈骗,导致老年人的养老钱被骗走。”江昱洁理解这种防范心理的来由,正是一些负面事件让老年人和家庭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江昱洁也观察到,现实生活中,无儿无女的老年人会遇到养老规划与生活照护上的难题。而即便有子女的部分老年人也可能面临“谁都指望不上”的局面。
新的形势下,信托重新进入人们视线。车耳介绍,信托既不是舶来品也不只是金融手段,而是一种古老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信托不是富人专属的融资工具,普通人同样可以运用。
在中国,大众对信托的认识仅局限于“金融工具”。江昱洁说,长期以来,信托做了大量例如发放贷款等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2023年国家出台信托业的“三分类”政策后,行业逐渐回归本源。信托公司可凭借其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等优势来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同时,信托这项工具,还可依据老年人意愿管理分配其财产、提供金融养老服务。
按照规定,在信托公司设立家族信托门槛需要1000万元、家庭信托门槛为100万元,现在,他们正在试点无门槛限的养老服务信托。昆仑信托首席顾问黄志斌告诉《财经》,一位50多岁的人士,没有子女。于是,他提前将自己的部分财产装入养老服务信托中,等到自己入住养老院,或父母生病需要治疗,信托公司将直接从信托账户财产中支付相关费用。
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上有90岁父母,下有一位脑瘫孩子。他在生前逐步将财产注入信托,以确保自己失能失智后,全家人的生活都能得到照料。譬如孩子进入医疗机构的费用,由信托逐月支付。信托框架下,还会另设监察人,将管钱和管事两件事分开。
将养老这件事托付给金融机构,中国仍在起步阶段。从2023年探索,截至今年7月末,昆仑信托成立了15单养老服务信托。他们还有一种设想,与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合作,将平台接入信托,老年人先享受养老服务,再由信托公司付款,避免社会机构卷款逃跑的风险。
但仅靠信托,尚不足以交付养老大事。意定监护也是不可或缺的配套制度。在中国,无子女老年人、失能失智老年人,做手术、入住养老院,都需要监护人签字,然而,由政府部门(民政局)、公益组织、公证处或律师来担任意定监护人,实践中仍面临重重阻碍。
今年两会,上海政协委员蒋碧艳在提案中指出,意定监护存在牵头部门不明晰问题。“民政、政法、医疗、金融、社工,具体落地涉及很多部门,实施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变数,谁来承担主要责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蒋浩指出,“有的社会组织如今有非常负责的管理人员,但三五年后换人了,服务的接续性能不能保证?机构的稳定性如何?”
这都是银发经济时代亟待解答的制度问题。在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看来,中国老龄社会将至少面临来自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育政策、乡村区域、社会服务、数字鸿沟,以及生命关怀的八大挑战。
江昱洁判断,随着老年人口占比逐渐增大,社会消费方式与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也会带动中国未来养老金融产业的转型。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课题组预测,人均消费水平中等增长速度,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为19.1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为27.8%,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9.6%;2050年银发经济规模为49.9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为35.1%,占GDP比重为12.5%。
“不是年轻人养老年人,而是老年人养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要拿工资、要挣钱。”江昱洁说,银发经济未来应是年轻人借科技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年人为服务付费的经济模式。而实际上,老年人不只是刻板印象中需要关怀的群体,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资本,这在日本社会的经验中已经得到验证。2021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修订后的《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日本企业可以为有意愿工作到70岁的老年人确保就业机会。年满65岁的企业员工可以自愿留在原公司,也可以选择到其他公司再干五年,直至70岁后退休。
日本发布的202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日本70岁-74岁群体的从业率达到33.3%,超过三成,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也就是说,在日本70岁-74岁的老人里,三人中就有一人还在工作。即使年龄超过70岁,只要身体足够健康,养老这件事,仍然可以托付给自己。
根据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2023年调查,中国60岁-69岁低龄老年人中有45%有就业意愿。张永利,这位退休的正县级干部,对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了如指掌,他向《财经》表示,现在依然希望通过其他渠道参与到招商引资中。70岁的朱红华退休前是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会计,也被企业返聘回了会计岗位上。“每天有些事情做,何乐而不为。”
在椿萱茂,工作人员邱钰程时常能感受到,他服务的长辈,每个人一生都经历了许多,他们的经验、判断、阅历,仿若一本活字典。“每位长辈打开,都是一本厚厚的书。”现今,图书馆里摆放着长辈带来的《鲁迅全集》,日本文学研究的泰斗也住这里。大厅二楼的走廊里展示着老人拼出的乐高养老院。和园的墙上,挂着的都是长辈一笔一笔所画的作品。
樊沈英的老伴,健康时天天坚持到书画室里写字。而今,他病倒接近500天。樊沈英慢慢释然了许多,“我守着他,觉得每一天都是我们额外获得的。”她决定珍惜天赐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