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岁读博,却像犯了错|一读·研选
编者按: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学术界,年轻的学者们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年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难题之一。Hugo Horta 和 Huan Li 合著的 《Ageism and age anxiety experienced by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in enacting a “successful” career in academia》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博士生在追求学术职业成功过程中遭遇的年龄主义和年龄焦虑问题,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年龄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成为衡量学术生涯成败的关键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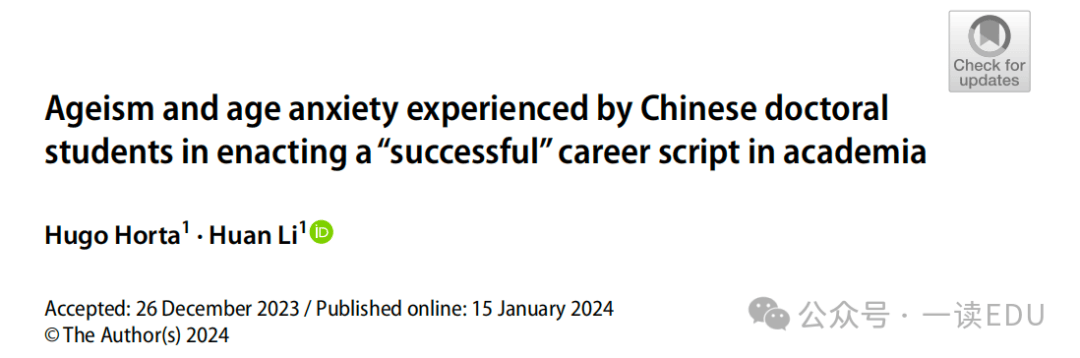
01
研究背景:学术职业中的年龄困境
在许多国家,大学为保留资深学者的经验和知识,允许他们延长退休年龄,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传承,但也引发了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对那些刚刚步入学术职业道路的年轻学者来说,他们面临着由于博士毕业生数量增加和稳定学术职位空缺减少而导致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中国,这种压力尤为显著。高校在学术招聘和研究资助申请方面,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年龄限制。比如,众多高校要求应聘讲师或助理教授职位的候选人年龄不得超过 35 岁;申请国家级青年科学基金时,男性年龄上限为35岁,女性为40岁 。这些硬性规定使得年轻学者在激烈的竞争之外,还要承受年龄带来的巨大焦虑,也降低了年长博士生和毕业生被选为学术职位的可能性,从而表现为年龄主义。
02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叙事探究方法(Narrative Inquiry)对7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10所顶尖大学的博士生进行了系统研究,重点考察他们在追求学术职业过程中面临的年龄歧视和年龄焦虑问题。
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注重样本的代表性。学科分布上,均衡覆盖理工科和人文社科领域;人口特征方面,涵盖不同性别和年龄段(25 岁以下至 35 岁以上)的受访者;学习阶段上,从博士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均有涉及。
数据收集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这种方法既能通过预设问题确保研究主题的聚焦性,又能根据访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问题,从而深入获取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和职业规划等质性数据。该研究访谈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10月期间通过在线方式完成,每次访谈平均时长为1小时。这种研究设计既保证了数据的丰富性和可靠性,又有效克服了特殊时期地理因素的研究条件限制。
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博士生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他们在博士期间的经历,他们对毕业后职业轨迹的规划,和他们对学术就业市场中自身优势和劣势的感知。
03
核心发现
1.年龄与职业发展
通过对70名博士生的访谈发现,学术职业中存在着一种“锦标赛”式的年龄剧本,即职业脚本(Career :学术职业中的“成功”路径被制度化,博士生内化这些标准并以此规划职业)。高校的招聘政策和研究资助申请规则塑造了这种脚本,要求年轻学者在特定年龄之前达到一系列关键的职业里程碑。例如,35岁之前获得青年科学基金,45岁之前获得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这些年龄限制不仅成为了衡量学术职业成功的关键标准,也在博士生中形成了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和年龄焦虑。
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有些人可能想要“躺平”,享受生活,也深知45岁之前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前期若没有取得成就,之后的职业生涯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换句话说,很多人觉得在年轻时必须努力争取一些重要的称号,这样才能在学术界获得成功。正如“马太效应”所描述的,早期获得成功的人能获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而那些晚些成功的人则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博士生们普遍认为,早早取得成就和称号是他们职业发展的关键。
在学术生涯中,年轻人还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与期望。这一过程可类比为一场游戏,游戏里有特定的规则和目标,比如在特定的年龄找到工作、结婚和生孩子。这些规则是由上一代人设定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必须遵循这些规则。比如,文中提到有人放弃工作去读博士,父母感到困惑和失望,因为他从一个有收入者变成了一个没有收入的学生。父母担心他年纪大了,未来不稳定,所以对他的选择表示反对。这就像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想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但老师和家长却希望他选那些“更安全”的科目。另一个人(MC13)也有类似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在学校待了太久,没有为家庭做贡献,所以希望能尽快毕业。这就像是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中,虽然他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他也知道时间不等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好成绩。
目前,大多数博士生选择了遵循现有的年龄与职业发展,但也有少数博士生试图挑战这一传统的职业规范。一些年龄较大的博士生对现有的年龄歧视表示不满,并计划通过在国外高校寻找工作机会来绕开国内的年龄限制。然而,这种选择并非易事,因为国外高校的竞争同样激烈,且对年龄的要求也不一定更为宽松。尽管少数博士生试图挑战这一脚本,但社会和家庭压力最终让大多数人选择顺从。一位年过35岁的博士生坦言:“我曾鄙视这种标准化的成功,但现在却因‘落后’而感到羞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开始选择回归主流的职业剧本,追求那些曾经被他们视为“成功”的职业目标。

2.职业追求的心理与策略
研究发现,参与者在职业追求过程中面临一种“锦标赛式”的职业发展模式,他们将在学术界找工作视为一场比赛,认为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认为,学术界的职位就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职位都已被占据,除非有人辞职或退休,否则很难有空缺的职位。举个例子,一个参与者说:“我到28岁才毕业,年龄是个大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觉得年龄越大,找到工作的机会就越少。像35岁是某些奖学金申请上限,如果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申请了。因此,他们认为早点找到工作更好,这样就可以在工作后再去国外进修或结婚。
其次,参与者们还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身精力和耐力似乎在下降。比如,一个人说他20岁的时候可以熬夜,但现在26岁了,熬夜会让他感到非常疲惫,恢复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像是一个运动员,年轻时能轻松跑得很快,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恢复能力变差了。
最后,研究发现参与者们的焦虑不仅仅是关于找工作的压力,还有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结婚和买房。他们觉得在职业上取得成功是他们生活的首要任务,其他的事情只能等到职业稳定后再考虑。这就像是一个学生在考试前只专注于学习,完全不考虑休息和娱乐,直到考试结束后才有时间放松。
3.女性博士的双重压力
博士生们在年轻时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年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学术职业的竞争环境,还与社会对年龄的普遍认知有关。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规范性的人生阶段模型,认为人们应该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完成特定的人生任务,如开始职业生涯、结婚生子等。这种模型与学术职业中的年龄剧本相互呼应,使得博士生们在追求职业成功的同时,还要面对个人生活规划的冲突。
对于女性博士生来说,这种冲突尤为明显。许多女性博士生面临着在职业发展和生育之间的艰难抉择。她们担心生育会耽误职业发展,因此选择推迟生育计划,因为“怀孕可能毁掉职业生涯”,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不仅影响个人选择,还可能加剧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一位女性博士生在访谈中表示:“我本应该在硕士阶段就生孩子,这样孩子现在就上小学了,会比现在好得多。但现在我快30岁了,才开始考虑要孩子。”这种年龄焦虑不仅影响了博士生的个人生活,还可能导致他们在学术职业中过度劳累,牺牲个人时间,以追求所谓的“成功”。
04
讨论
这项研究探讨了在学术界中,年龄歧视是如何发生和被延续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希望成为学者的博士生,他们在追求学术职业时所面临的与年龄相关的限制和偏见。而职业脚本就像是一个游戏规则,告诉你在这个游戏中应该怎么做才能赢。学术界的这些规则让博士生们觉得,只有按照这些被认为是“成功”的路径走,才能被认可和接受。这些规则在不同学科之间几乎没有变化。博士生们通过与同龄人和其他人的社交互动,逐渐内化了这些成功的标准,并对那些不遵循这些路径的人产生偏见。
研究发现,博士生普遍将职业脚本置于生活脚本(如成家、生育)之上,尤其是女性博士生面临更严重的职业与家庭抉择困境。年龄门槛迫使她们推迟生育,可能对国家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学术职业路径被比作一场年龄敏感的锦标赛:年轻、高产、高效成为成功标准。博士生必须在既定年龄前达成目标(如获得人才称号),否则会被边缘化。这种竞争文化加剧了焦虑和短期功利主义。
例如,如果一个博士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职业道路,可能会被同学们视为“失败者”,这种认知让他们感到害怕,因此他们最终会选择遵循这些主流的职业规划。研究还发现,博士生们对招聘中年龄歧视的看法与已有的文献相符,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他们认为年龄增长会导致身体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工作效率,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成熟和经验带来的好处。其次,他们担心高层学者可能会觉得年长的员工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在一些文化中,年龄与地位有很强的关联。
这些因素,加上基于年龄的招聘政策,使得年长博士生在完成学业后,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职业前景都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研究者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年长博士生如何在这些挑战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并为创造一个更友好的社会提供政策建议。
然而,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探讨博士生如何在结构性限制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干预缓解年龄歧视。核心启示在于,中国学术界的年龄歧视已从职场前移至博士生培养阶段,形成系统性压力。改革需同时关注制度设计(如弹性年龄政策)和文化观念(如对“成功”的多元化定义)。

05
结语
Horta 和 Li 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学术职业困境的机会。通过揭示年龄剧本的存在及其对博士生的影响,文章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年龄主义在学术领域表现形式的认识,还为改善学术职业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的年龄限制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职业的规范化和效率化,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加剧了博士生的年龄焦虑、限制了学术职业的多样性、对女性博士生的职业发展造成阻碍等。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以年龄为门槛的学术评价体系,并提出警示:当前模式虽能短期提升科研产出,却可能扼杀学术多样性,削弱学术界与社会的联结。例如:学校招聘时,可以考虑放宽对年龄的硬性要求,更加注重学者的学术能力和潜力,而不是单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此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可以为博士生提供更多的职业规划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年龄焦虑,平衡职业发展与个人生活。
